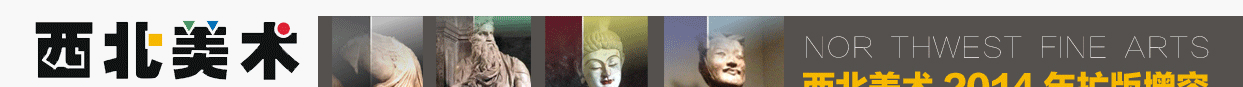摘要:飞廉作为一种流传有绪的有翼神兽,主要用于装饰钟虡、磬虡或其座子(趺)。其形制可分本土和含有外来形式因素的两种,战国时期初见端倪,西汉时期逐渐统一,风格化显著。汉武帝时在长安仙观上雕造的铜飞廉,是该母题中具有标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杰作,影响巨大而深远。
关键词:早期;有翼神兽;笋虡;趺(座子);飞廉;功能;形制
本文讨论的是东汉之前的有翼神兽问题。
中国古代将悬挂编钟、编磬的支架称作笋虡,笋为架上横梁,虡为架两边的立柱(包括座子)。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互证,可知早期有翼神兽与一种叫飞廉的动物母题有关,而该母题主要用于装饰钟虡、磬虡或其座子。
一、先秦时期装饰笋虡的动物母题
重视和讲究笋虡装饰雕刻是先秦时期礼乐器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做法在《考工记·梓人为笋虡》有专门记载。该篇将动物母题归纳为臝属、羽属和鳞属三种:臝属“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宜;大声而宏”,用于装饰钟虡;羽属“小体骞腹”“恒无力而轻,其声清阳而远闻”,用于装饰磬虡;鳞属“小首而长,抟身而鸿”,为钟、磬支架的笋部所通用。关于它们的含义,《考工记》郑玄注曰:“臝者,谓虎豹貔螭,为兽浅毛者之属。羽,鸟属。鳞,龙蛇之属。”此说不确,需要补充。其中,臝同倮(裸),人为“倮之虫三百六十”(《大戴礼记·易本命》)之一,也是臝属中的一种母题;羽属,不仅指鸟类,还包括鸟兽合体的有翼神兽。
早年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的石虎和石枭,可能是我们目前所见先秦时期采用动物母题装饰乐架座子的最早实例。石虎呈蹲踞状,高37.1厘米,头似猛虎,坐姿像人;石枭作站立姿,高33.6厘米,整体为猛禽形象,双足却作兽足。它们的背后皆刻有凹槽,大约用以嵌插木制立柱。楚戈先生认为石虎(臝属)为钟虡插座,石枭(羽属)为磬虡插座,(1)意见可取。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编磬一架,装饰磬虡的是一对青铜翼兽(图1),头小,张口吐舌,两颊伸出弯曲的双角,颈部细长,体宽而肥厚,双翼平张,尾扁而短,四只爪足,可归为羽属。在功能和造型上,它与河南淅川徐家岭楚墓(春秋晚期)出土青铜神兽存在着继承关系。同墓出土的一件鸳鸯漆盒,器腹两侧各绘有一图。左侧是撞钟击磬图(图2),乐架上分层悬挂甬钟、石磬各两枚,笋列树羽,虡作猛兽形,口衔笋端,上唇卷起,长颈,爪足,臝、羽二属兼之。
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铜壶镶嵌宴乐攻战图像,图中编钟、编磬同悬一座乐架(图3),笋部采用鳞属母题,虡部则为一对大鸟,弯颈挺胸,器宇轩昂,是为羽属。河南辉县战国晚期墓葬出土一件刻纹铜奁(残),器腹可见一组乐舞图像,位于建鼓之右的乐架上悬挂编钟(图4),虡部作猛兽形象,口张开,上唇翻卷,屈颈挺胸,尾巴翘举,前肢前屈,后肢蹬踞,是为臝属。
中山国原名鲜虞,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建立的国家。河北平山战国晚期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银青铜翼兽(图5),共4件,两件一组,分别放置在该墓的东库和西库中。(2)东库两件头朝左,另有帐具等生活类器物伴出;西库两件头朝右,伴出铜、陶礼器和乐器、玉器等。青铜翼兽长40厘米,高24厘米,兽头如狮虎,张口露齿,桃形鼻子和双耳,两肋羽翼修长,四肢迈开,情态凶顽,腹底“十四祀,左使库,啬夫孙固,工隰,冢”13字铭文,为制器年代和工匠、监造官吏名。它们的重心很低,脊背前部呈人字坡形,可能为承托器物之专用,或是对原有插座(孔)改造所致,不排除配饰乐架的可能。
出土实物所反映的钟虡、磬虡装饰情况,与文献记载的规制大致吻合。其中,采用有翼神兽母题始于战国时期,之前的未见,其形制可分本土和含有外来形式因素的两种,且南北地域特征显著。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青铜翼兽属于传统作风,是我们目前能够确定的该母题装饰磬虡年代最早的作品。晚期中山王墓的青铜翼兽含有外来形式因素,最为学术界关注和热议。李学勤先生说它的形象“非中原艺术原有者”“和斯基泰的有些花纹相似”,并引用乌恩先生关于狮身鹰头兽“这种艺术母题和风格在战国晚期被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借鉴”的意见作为支持。(3)我们则以为,中山王墓青铜翼兽与大英博物馆藏斯基泰金饰件(图6)上的翼兽形象相近,而与狮身鹰头兽相远。但它并不失本土尤其是三晋青铜器做派,如可能用以配饰器物的功能,以及成熟的圆雕形式和通体错银纹饰等,都是域外小型饰件所不能相比的。
二、西汉时期装饰钟虡、磬虡的有翼神兽
秦代暂无遗物可寻,付之阙如。到西汉时期,有翼神兽母题不仅装饰磬虡,也为钟虡所用,这从文献和出土文物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当时长安宫中“列钟虡于中庭”(《西都赋》),装饰钟虡是“奋翅而腾骧”的有翼神兽。《文选·西京赋》李善引薛综注:
洪钟万钧,猛虡趪趪。薛综: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钧。悬钟格曰笋,植曰虡。趪趪,张设貌。言大钟乃重三十万斤。虡力猛怒,故能胜之焉。李善:《周礼》曰:凫氏写兽之形,大声有力者,以为钟虡。虡,音巨。趪,音黄。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薛综:当笋下为两飞兽,以背负,又以板置上,名为业。腾,超也。骧,驰也。言兽负此笋业已重,乃有余力奋其两翼,如将超驰者矣。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安北郊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陶翼兽备受学术界关注。它们皆为乐架的座子,主要有以下几批:(4)
红庙坡陶翼兽(图7),共有2件,同墓还出土有陶编钟、编磬,以及陶瑟和陶仓、熏等。陶翼兽吻部长而扁,长耳向后,两肋羽翼系装配而成,长尾上举,前肢伏卧,后肢蹬踞,脊背前端有承插器物的长方形孔洞。
马乎沱陶翼兽(图8),仅见1件,属于收缴文物,墓葬的具体情况不明。陶翼兽胸部长须及地,上唇有肉角(或唇须),眉弓突出,两肋饰三道长羽翼并收于臀部,前肢前扑,后肢蹬踞,颈背交接处有方形插座。
范南村陶翼兽,出自M92、M120号墓,共有4件,造型与马乎沱陶翼兽基本相近,同时还出土陶凤龟座4件。其中,M92号墓陶翼兽旁边伴有陶编钟和编磬,M120号墓陶翼兽旁边伴有陶编钟,两墓陶凤龟座旁边皆伴有陶编磬。
十里铺陶翼兽(图9),共有4件,同时还出土有陶编钟磬、编钟等。陶翼兽吻部较短,张口吐舌,颔下和胸部垂须,双翅并收拢于臀部,长尾折举,颈背有方形插座。
以上四个出土地点的陶翼兽,马乎沱和范南村的为一式,红庙坡和十里铺的各为一式。它们的颈背处都有插接立柱(虡)的插座或插孔,除马乎沱的外,其他三个地点伴出陶编钟和编磬。
2012年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青铜明器编钟、编磬各一套,(5)装饰钟虡座子为一对青铜卷唇兽,装饰磬虡座子则是一对青铜翼兽(图10),合乎《考工记·梓人为笋虡》所论臝、羽二属各自的功能。青铜翼兽长46厘米,高约21厘米(连虡通高86.5厘米),上唇饰有肉角(或唇须),头顶有双角,胸前长须及地,两肋有三道修长的羽翼,尾长而细,爪足,前足前伸,后足蹬踞,脊背前部有孔洞,插置圆柱形的虡(残),通体饰以云气纹,形制与西安马乎沱和范南村陶翼兽比较接近。大云山一号墓是西汉江都国第一代国王刘非的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28年或稍后的一段时间内。
据《旧唐书·音乐二》记载:
乐悬,横曰笋,竖曰虡。饰笋以飞龙,饰趺以飞廉,钟虡以挚兽,磬虡以挚鸟,上列树羽,旁垂流苏,周制也。
“趺”即安插“乐悬”(悬挂编钟、编磬)架子的底座,可看作虡或其构件,而采用飞廉母题作装饰,则是周代以来的制度。据此可推定,西安北郊汉墓陶翼兽和大云山江都王墓青铜有翼神兽,皆称名飞廉。它们虽为丧葬而专门制作的明器,但未失先秦礼乐器的装饰传统及规制。安徽阜阳红旗中学出土的汉代青铜翼兽,其背部有插孔及插柱,亦为“饰趺”的飞廉。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青铜翼兽形饰,共有8件。(6)Ⅰ型(图11)4件,兽首高昂,躯干分开,作90度夹角(内有朽木),双角卷于背上,两肋羽翼修长,四肢及躯干矫健有力,造型与大云山江都王墓青铜翼兽相近。Ⅱ型4件,形似鹿,背饰飞翼,臀部内侧有插钉。参考飞廉母题的装饰功能,推测它们原来装饰在木制器座的棱角处,而器座可能为“乐悬”之用。
汉元帝渭陵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玉雕翼兽(习称玉辟邪)两件,分别发现于1966年和1973年。先发现的头饰双角,体态硕壮,前肢前伸,后肢蹬踞(图12);后发现的头饰独角,作爬走状。据刘云辉先生调查并复原,后者出土时与两枚大小不同的套在一起的微型鎏金编钟,放置在通高仅8厘米的带盖鎏金的微型铜鼎内。(7)这个材料十分重要,说明它与微型鎏金编钟存在着配饰与被配饰的关系。这件玉雕形体太小,不宜在背上凿出插置虡(立柱)的孔洞,推测它原来摆放在微型鎏金编钟旁边,而先发现的那件双角翼兽,用途相同。出自宝鸡东汉吕仁墓的玉(石)雕翼兽可作旁证,该器形体很大,背部雕出方形和圆形插柱。
西安北郊汉墓陶翼兽出土后,考古研究人员曾提出质疑:“参照曾侯乙墓内作为磬架的两件铜怪兽,汉代早期的这些翼兽为编钟和编磬的支架座子是没有问题的。疑问是为何在墓中要随葬这种造型的兽俑?”(8)我们以为,用作装饰笋虡座子的飞廉母题,除传承并发展先秦以来臝、羽二属的装饰功能之外,还与礼乐娱神的传统观念和汉时全社会弥漫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长沙马王堆汉墓铭旌的上部象征天庭,中心处有一对相背奔跃的卷唇神兽牵引甬钟(图13);长沙砂子塘汉墓漆棺的足挡绘有悬挂特磬和甬钟的画面,特磬的股、鼓上有相向而卧的羽人及神豹。
汉武帝执政以后,随着对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通往西域的道路打通,中西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出现互动,有翼神兽的形制随之有了较大变化:早期的西安北郊汉墓陶翼兽,延续前代作风,传统鹿、龙造型元素较多;中期的江都王墓和中山靖王墓青铜翼兽,形制趋于统一,风格化显著;晚期的汉元帝渭陵玉雕翼兽,域外狮首格力芬(lion griffin)或带翼狮(winged lion)的形式因素增强。
三、关于飞廉
飞廉又写作“蜚廉”,东汉以来的学者在注释前代文献时,对其属性、功能及形象特征都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和描述。王逸《楚辞章句》:
《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飞廉,风伯也。
《九辩》: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王逸:风伯次且,而扫尘也。
《远游》: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王逸:风伯先导以开径也。
再如高诱、郭璞、应劭、晋灼的解释和描述:
《淮南子·俶真训》:若乎真人,则动溶於至虚,而游於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於方外,休乎宇内。高诱:蜚廉,兽名,长毛,有翼。
《上林赋》:椎飞廉,弄獬豸。郭璞: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
《史记·孝武本纪》: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侯神人。应劭:飞廉神禽,能致风气。晋灼: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
综之,飞廉是神禽(按:禽是鸟兽总称)或神兽,能致风气,给游天者启路开道,或作为升仙者遨游天际的乘骑。它有鸟兽合体的外形特征,兼有臝、羽二属,诸家说法不尽相同,可能因参照不同文献及艺术作品所致。其中,高诱描述的飞廉形态,与西汉的陶塑、青铜及玉雕翼兽的造型相差不大;郭璞、晋灼描述的飞廉形态,孙机先生讨论过,但他的举证皆为东汉以后的作品。(9)曾侯乙墓用作悬鼓的青铜鹿角立鹤,为凤鸟之变形,不会是飞廉。李零先生认为飞廉“是像草原鹰首鹿那样的动物”,(10)但这种艺术形象与汉晋学者描述的飞廉相去甚远,而且在中原地区未见出现。
在考释飞廉的方面,早年孙作云先生用力最多,并在多篇论文中连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11)他认为早期的飞廉即凤鸟,古语“凤”与“风”同字,“风”字古音“孛缆”,而飞廉为“孛缆”之音转,“古人相信风的生由于凤之飞,所以在传说上又说它是风神”。又说:“它先是神禽,在汉代神仙思想弥漫一切时,又变成人们升仙骑乘的四脚兽。”“汉武帝作飞廉馆,汉明帝迎取飞廉像,皆是为了求神仙。他们认为骑飞廉,或跟着飞廉飞,就可以成仙的。”他考证飞廉为“孛缆”(风)之音转,尚需再讨论,但其他的意见还是可参考的。
从字词的构成上看,“飞廉”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合成词,“飞”表其能在天空飞翔,“廉”(来母谈部字)与“麟”(来母真部字)的上古音,以及“麟”的异体字“麐”、偏旁部首“鹿”都比较相近。所以我们怀疑“廉”或许是“麟”的假借字或别字,飞廉一词原来指能在天空中飞翔、形似鹿的神兽,或说它的本义是有羽翼能飞翔的麟。麟也是五灵兽之一,代表中央土,其虫臝,麒麟为后来的扩展名。
飞廉又名“龙爵”,古代“爵”与“雀”通假,龙爵即龙雀,亦即飞廉。它也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合成词,表形似龙的神雀或有羽翼形似龙的神兽之义。山东苍山城前村汉墓画像石有“龙爵除殃鹤啄鱼”题记,参考研究者的对读意见,(12)“龙爵除殃”对应的是墓门横梁背面画像的上栏左面一对相向而戏的翼兽(右面为“鹤啄鱼”)。在山东滕州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石翼兽中,出土于张汪镇洛庄村的一件最重要,(13)它残高0.96米,长1.45米,胸部刻有篆书“龙爵”两个大字(图14)。东汉同石翼兽另有“天禄”“辟邪”(如州辅、宗资墓的)题铭,属于吉语冠名,并非本名。
四、长安仙观上的铜飞廉
在飞廉神兽的传承与演变中,享有盛名的莫过于汉武帝时在长安飞廉观上雕造的大型铜飞廉。此事为当时重大事件,《史记》《汉书》皆有记载,后来《三辅黄图》(卷五)还有综述:
飞廉观,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作。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铜铸置观上,因以为名。班固《汉武故事》曰:“公孙卿言神人见于东莱山,欲见天子。上于是幸缑氏,登东莱,留数日,无所见,惟见大人迹。上怒公孙卿之无应,卿惧诛,乃因卫青白上云:‘仙人可见,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为观于缑氏,则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不极高显,神终不降也。’于是上于长安作飞廉观,高四十丈,于甘泉作益延寿观,亦如之。”
长安飞廉观属于祀神求仙建筑,铜飞廉用以降神迎仙,所以成为仙观的标志和象征。据何清谷先生考证,飞廉观大约在丰、镐之东的上林苑某个苑门附近,距离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西南的上兰观不太远。(14)观是宫苑门前的双阙,配饰飞廉观的铜飞廉或为一对,而且形制考究,体量巨大。铜飞廉铸于元封二年(前109年),永平五年(62年)汉明帝将其与未央宫铜马一并东迁洛阳,列置在上西门外的平乐观。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雒(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后汉书·董卓列传》),铜飞廉遂遭销毁。张衡《东京赋》对东迁来的铜飞廉有描述:
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
《文选》李善注: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
“蟠蜿”,盘伏屈曲貌也,说明铜飞廉汲取了长体动物的造型元素;“瑰异谲诡”“规遵王度,动中得趣”,是对它帝王气派和寻常风格的礼赞。文学作品多虚写,造型细节未及。同时期同母题的出土实物,即前文所论西汉中期王侯墓的青铜翼兽,晚期汉帝陵园的玉雕翼兽,都是我们推定铜飞廉形貌的可靠依据。在汉武帝茂陵“瓦渣沟”遗址出土一件空心砖,边栏装饰羽人驭兽的二方连续图案(图15),左面羽人驭龙,右面羽人的乘骑不是虎,而是有羽翼的神兽。神兽头部饰角,颈部有鬣毛,身饰豹斑,肩胛处有宽而短的羽翼,长尾上举,四肢交叉作疾走状。我们怀疑,它可能刻画的是飞廉形象,可能受飞廉观上铜飞廉的影响。
具有完全独立性质的长安铜飞廉,凝聚着汉武帝祀神升仙的激情和长安雕塑匠师的非凡创造力,它既是有翼神兽装饰功能的扩展,又是这一雕塑样式的升华,同时还具有标型意义和示范作用。
五、余论
讨论中国早期有翼神兽,除关注它的外在的形式外,内在的功能意义也不容忽视。飞廉作为一种流传有绪的艺术母题,主要用于装饰钟虡、磬虡或其座子,反映的是传统礼乐器的规制及其艺术理念。到汉武帝执政时,它的装饰功能发生了重大改变,摇身为长安仙观的标志和象征之物。
中国有翼神兽自有传统,并非都是“舶来品”。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M4)新出土青铜牺尊(图16),头及身似鹿,有双角,爪足,腹侧装饰三道修长的羽纹,它是我们目前所知形象明确、年代最早的中国式有翼神兽。含有外来形式因素的有翼神兽,战国晚期始现端倪,发生地点接近北方草原。到了西汉中期,有翼神兽的形制已趋向统一,风格化显著,受外来狮子形象影响较多。其中,长安铜飞廉堪称划时代的杰作,意义重大并影响深远。
长安铜飞廉东迁洛阳之后,必然给迁移地带来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在今洛阳孟津油坊村西500米,汉光武帝原陵东南约1000米处发现一件大型石翼兽(图17),经文物部门鉴定,确认是该陵神道上的石雕。(15)石翼兽原为一对,已发现的这件高190厘米,长297厘米,是东汉石翼兽中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造型完美及雕刻手法成熟的作品,标志着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它腹下凿空,交叉的四肢、抛物线式长尾落于受力的托板,全然没有早期循石造型之风,却与之前青铜、玉雕翼兽的形制及风格相似。我们推测,石雕很可能是由青铜雕塑“移植”而来的,其范本非长安铜飞廉莫属,而雕造契机又与汉明帝在原陵推行上陵礼,以及在陵园神道上列置大型石雕有直接关系。(16)换言之,东汉大型石翼兽的兴起,原陵开风气之先。
注 释:
(1)楚戈:《人兽之间——殷墟的石雕艺术》,载《故宫文物月刊》1983年1卷第3期,第34-51页。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1期,第5-8页。
(3)李学勤:《虎噬鹿器与有翼神兽》《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4页。
(4)林通雁:《西都——汉长安城美术史迹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325页。
(5)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广新局:《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载《考古》2013年第10期,第19-23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97页、下册图版五六。
(7)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研究》《陕西出土汉代玉器》,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8)韩保全、程林泉、韩国河:《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9)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10)李零《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11)孙作云考释飞廉的论文主要有:《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氏族之研究》《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敦煌画中的神怪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考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画幡》《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雕像考释》等,现已收入《孙作云文集》第3、4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巫鸿:《超越“大限”——苍山石刻与墓葬叙事画像》《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6页。
(13)滕州市文化局:《滕州文化志》,枣庄市新闻出版局1997年印制,第310页;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志》(初稿),第40页。
(1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9页。
(15)张雁雁:《汉光武帝原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阎崇东《西汉帝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16)《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58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随着每年正月上陵礼的推行,汉明帝又将八月在宗庙举行的饮酎礼也移至原陵来举行。《水经注·阴沟水》说:曹嵩墓前“夹碑东西,列对两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可知原陵神道列有象、马等大型石兽。
林通雁,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