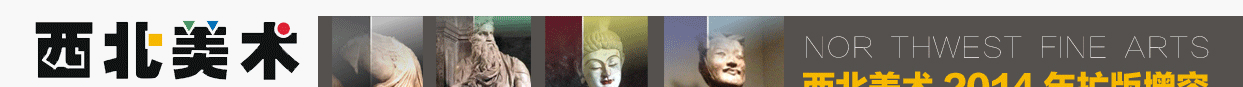黄胄以速写造型直接进入水墨人物画的探索,被认为是素描造型加笔墨这一解决20世纪写实人物画基本方案的另一种类型,他激情恣肆的平直用线一改此前和同时代其他人物画家的用笔方式,多条速写式的复线运用也最生动鲜活地诠释了动态之中的人物与动物形象。显然,他笔线的写意较少一波三折,而是笔速的迅猛飞动,从而使速写式的笔线与富有弹性的笔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这种典型的黄胄“腔调”,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甚至他的成名作《洪荒风雪》仍然体现了有笔有墨的造型方法,这和他后来形成的典型黄胄画风并不完全相同。那么,他是怎样从《洪荒风雪》变出,又是在哪个时间、哪些作品中完成了黄式画风的转型的呢?笔者以为,从1955年的《洪荒风雪》到1962年的《奔腾急》,黄胄完成了他艺术风格上最重要的一次艺术突变,从此之后黄胄的画风基本定格,此后近半生的绘画生涯只是这种画风的延续、完善和更加饱满的发挥。
一、《洪荒风雪》作为50年代中期中国人物画的典型笔墨样式
并未进入美术学院进行系统人物造型训练的黄胄,几乎是在追随赵望云、韩乐然的西北写生旅行中逐步完成自我造型训练的,但他不是为造型训练而速写,而是和赵望云、韩乐然一样在用毛笔描绘其时艰辛的民生形象中自然完成的。因而,黄胄40年代的写生人物画具有赵望云式的简化却细劲的笔线勾形特征。譬如,1943年黄胄的陕西千阳写生,虽然速写的人物造型还显得松散,但勾线用的倒是传统的游丝描,细劲有力。两年后他的黄泛区写生,譬如《流民》,已开始出现较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较复杂的人物组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的远近是用墨的浓淡与疏密来体现的。而且,笔线细而长而柔,也即在造型与笔墨之关系上,较重后者。再如《家住水晶宫》,这一特点更加鲜明,人物造型尚不能体现结构与解剖关系,主要通过细长劲挺而柔韧的线条予以弥补;人物衣着与河滩、远景的淡墨运用,也增添了画作的笔墨意趣。应当说,在1946年的《小秃儿》《行行好吧,大娘》和《伊斯兰的小贩》一些放大了的单体人物形象描绘上,可以看出黄胄人物写生能力的逐步增强,随之也能看到其用笔的灵活与笔法的多变。至此,可以说黄胄十分注重笔线粗细浓淡的变化,并未以造型的精准来抑制笔墨意蕴的发挥。
这种注重用笔用墨的人物画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军民一家》《爹去打老蒋》《打马球》等都十分重视大块墨色在勾线中的穿插。尤其是《爹去打老蒋》(1950)作品里母亲的围兜、身边的小狗和爹爹身边那一匹占据画面主体的马,都是用温润的墨色去塑造的。这表明那个时期的黄胄颇注重笔墨结合的方法塑造形象,甚至墨色的块面感亦十分突出。但《打马球》(1953)作品中的马虽以不同墨色来塑造,但各种姿态生动的人物形象却显示了黄胄造型能力的较大提高。而其早期的名作《苹果花开的时候》(1951),则开始放大早期画面的人物形象,其歌舞中的维族男女也揭示了黄胄造型能力的提升。兼工带写的语言,使人物轮廓勾线比此前更加肯定稳健,其笔线特征是较为纯粹的中国画白描。但黄胄的个性是写意的,此后,他便逐渐从这种白描转向水墨意笔,但人物形象仍相对严谨,笔线服从于形象的塑造,如《玉龙喀什河边》(1953)、《帐篷小学》(1954)、《幸福的道路》(1955)等。这些画中的人物形象,都处在一种日常生活的即时动作中,而不是亮相式的。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黄胄人物画面貌与同代人的最大区别,这就是他的人物形象择取于生活的瞬间,具有人物姿态的原生性,而不是几经修饰的人物造型,这便促使他更多地通过速写来记录这些人物生活形象的自然美。譬如,《玉龙喀什河边》画面上所刻画的那个背着浮球的姑娘,并未着眼于告知人们她要做什么,而完全以她生动的体态来确立此作的审美视点——她背负浮球眺望远方的瞬间呈现的造型美感。此作和《帐篷小学》《幸福的道路》的区别,还在于速写形象的直接使用,从而开启了黄胄那种速写式直线的人物形象塑造。
应当说,真正奠定黄胄在现代人物画史地位的《洪荒风雪》(原名《柴达木的风雪》,1955),是在《玉龙喀什河边》《帐篷小学》和《幸福的道路》创作经验基础上的一次飞跃,他将《帐篷小学》和《幸福的道路》作品中写意笔墨与扎实生动的人物造型结合起来,画得更加放松,也更加自由,尤其是占据画面主体位置的骆驼完全以赭石和水墨泼写而出,皮纸的无笔痕渗化显现出墨色特有的温润,而人物也以笔墨结合的方式塑造,皮大衣的翻毛更加凸显了笔墨的激情飞写。显然,该作是对黄胄此前画法的总结——造型的生动准确与笔墨的自由挥写几乎达到完美的境地,但这种画法仍和他后来被认定的黄式凸显平直复线的画风存在颇多的差异。如果我们横向比较这个时期其他知名人物画作品,如汤文选《婆媳上冬学》(1954)、周昌谷《两个羊羔》(1954)、杨之光《一辈子第一回》(1954)和方增先《粒粒皆辛苦》(1955)等,大多都处在新中国50年代中前期写实人物画探索的共同特征上,这就是速写与传统白描结合而画大的人物体态,素描与写意笔墨糅合画人物的头像,他们画风的微妙区别往往在于人物造型实写的程度以及个性化的笔墨风貌上。黄胄的《洪荒风雪》虽也用此法,但人物形象动态感的捕捉似乎更加纯熟和自由,而不像其他画家的拘谨和生拙。
《洪荒风雪》之后,黄胄的人物画进入了一个既延续这种随造型要求而呈现笔墨枯湿浓淡变化的人物画创作,也呈现了逐渐将速写线条嵌入人物形象塑造的并行状态。前者,最典型的是他于1978年补款的画于60年代初的《出诊》,画面以淡墨淋漓的骆驼、牧羊犬、藏女皮帽为画面主体,出诊女医生形象的部分勾线只起辅助作用;后者比较突出地呈现在《缫丝女工》(1957)、《育羔》(1957)等作品中,这些画作虽还保留了部分淡墨塑形,但人物主体表现均出现了硬挺的轮廓线,一改此前顿挫使转、柔和流畅的白描。
二、变法的桥梁:《巧阿姨》与《红旗谱》插图
从1959年到1961年,黄胄的人物画都处于变法的转型期。一方面,他延续《帐篷小学》和《幸福的道路》那种兼工带写的画法,画出了《丰乐图》(1959)具有上百个不同人物造型的大型群体人物画巨作,其人物的勾线偏重于白描式的写意,在严谨的人物造型中适度呈现写意的特点,这在《载歌行》(1959)画作上同样可见这种中国画的用线方法——以笔带墨,具有粗细、浓淡、顿挫、使转、虚实的笔线变化,毛驴、衣着等适当以淡墨色块晕染和穿插。另一方面,他试图将速写的人物造型直接搬用到画面上,出现了速写式的人物造型,从而使速写直线混搭于笔墨曲线,较典型的作品有《新生》(1959)、《巧阿姨》(1960)、《僮族老妇人》(1960)等。《新生》画作上女医生和藏女大的结构线,仍具有笔墨的使转变化,但肩线和手臂衣纹略呈平直线条;《巧阿姨》画面上三个幼儿园阿姨的形象均来自现场速写素材,因而除了素材上人物动态的搬用,捕捉这些动作的速写线条也被直接引用,如处于画面上端背对观者的阿姨的整个形象塑造,几乎完全是平直勾线,而且为突出女性背部优美的肩、臀,画面不惜反复用线予以强化。或许这种复线强化形成了过重的墨色,画家又用白线勾画以图减轻其重度。墨线的反复勾画与白线的减轻,其实都形成了其爽利、干脆的复线效果。相对而言,这种用线方法在近前的两个阿姨形象上就没有全部出现,最前阿姨的身体以淡墨勾写为主体,具有浓郁的水墨味,但脸部、手部却具有速写用线的特征。应当说,《巧阿姨》是一幅从笔墨用线到速写用线并用的画作,最能揭示黄胄变法的过程。同样,《僮族老妇人》也是笔墨用线与速写用线的混合体,老妇人体态的大线具有骨法用笔的凝重、苍辣,但线条的顿挫使转已开始连成一体,不见断笔,这和同代其他人物画家以断笔的方式体现笔墨变化的线不同;而老妇人的脸、手、脚几乎是平直的速写线条,平滑而爽利。
1959年黄胄开始构思创作在当时反响强烈的《红旗谱》插图,其中一些作品更明显地凸显硬挺、豪爽、泼辣的速写笔线,水墨意蕴相对处于辅助地位。如《春兰》(1959)以席地而坐、后半侧少女形象为画面主体,人物形象几乎直接移用了速写造型,因而画作也用一种浓墨勾廓和塑造,平直用线的力度来自速写原型,从而改变了此前较为曲折的圆线,其笔墨的痛快显然是通过这种疾速而平直的线随兴写出。黄胄对塑造女性形象的敏感,也于此得到了揭示——女性正侧面、修长的颈部及削肩、秀巧的指形等,这些女性优美的造型从此也几乎成为黄胄独特的人物造型语汇。《红旗谱》插图创作延续的时间较长,这既可看出黄胄为寻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而煞费苦心,也可看出他从速写吸取养分的艰苦探索。《胜利归来》描绘的众多村民形象,既有笔墨意蕴也夹杂着较多速写的直线。现在保留的些许草图,或更能揭示这一混杂的转换过程。如1961年的《严萍》,纯用焦墨勾画,已没有国画白描的痕迹,严萍右肩因抬高肩膀而进行的矫正性复线,恰恰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老奶奶》(1962)、《朱老明》(1962)是介于速写与焦墨勾线之间的转换,抑或是作者为表现对对象的感受,而不计较速写与焦墨勾廓之间的区别。画于1962年的《春兰》是这套组画中最为知名的一幅,画作以四分之三人面侧度塑造了一个端庄秀美的女性形象,全画虽在头发、衣着上以水墨画出,但浓重粗黑的人物轮廓线画得干脆而果断,春兰在炕上生动的坐姿,是通过复线的调整获得了似静而动的效果。在1962年画的《朱老筑、严志祥和小虎子》中,正面叉腰站立的朱老筑、严志祥均以粗而浓的大轮廓线加强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感,复线的运用使形象显得活泼生动。而《朱老忠》(1962)、《运涛与春兰》(1962)看似增添了水墨成分,但从速写转换来的平直而刚健的线条却始终主导着形象塑造方式。从画家为《红旗谱》插图所进行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速写来看,画家似乎一直难舍对速写人物形象真切生动感的表现,这种不断加强的人物轮廓线条,或许也只是他为呈现这种造型而进行的笔墨调整。因而,就黄胄个人创作历程而言,历时4年的《红旗谱》插图创作也是完成其艺术变法的桥梁和纽带。
三、1962年新疆西藏题材完成的变法之旅
黄胄艺术变法完成于1962年。这一年他的艺术创作出现了井喷,创作了诸多进入艺术史的大作,而完成他艺术变法的则是本年创作的新疆、西藏题材的作品。
1962年(元旦前夕)再度翻作《祖国的眼睛》的《巡逻图》是此年的开篇之作,也是黄胄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此作虽因渲染风雪而降低人物塑造用墨的浓度,但人物、军马的轮廓线却异常分明。如果把此作和《洪荒风雪》进行比对,便不难发现黄胄在笔墨与造型关系处理上的不同。《洪荒风雪》以大块浓淡结合的笔墨来塑造骆驼和勘探队员,而《巡逻图》却以平直的轮廓大线来塑造,淡墨、浓墨都只起辅助作用,这正是黄胄渐进地完成变法后的典型样本。作为新疆民族形象的歌手,黄胄或许只有在纵情描绘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维族、塔族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时,才能真正完成他的艺术变法。在黄式速写入画的风格形成上,1962年的《和阗姑娘》《新疆舞》《黑娜其罕》等画于新疆喀什、阿克苏等地的新疆人物形象,几乎完整地呈现了他此后始终坚守的黄胄独特风貌。《和阗姑娘》以大半身舞蹈中的维族姑娘为画面主体,在体态处理上夸张了肩颈、丰胸、细腰和半蹲的臀部,从而有力地描绘了维族舞蹈婀娜多姿、顾盼生辉的舞姿。这种富有古典美的动态感的造型,促使画家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来捕捉,其笔线首先在于对这种瞬间即逝美感的捕捉,笔线既连贯也不断地出现复笔予以动作表现的矫正、调整和加强,线条以细劲平直为主,也因速度作用而增添了这些线条的劲挺和弹性,大块墨色降低到最少的程度,尤其是大块的修饰性的墨色几乎绝去,画面把最焦浓的那几笔留在最后,再度强化肩、肘、腰、臀这几处素描处理上必须予以凸显的部位。黄胄在此作显现出的他对人体素描的理解是深刻的,这就是“致广大”以抓取人体变动的大关系,“近精微”在描绘人物眉目、手势等方面的细致刻画。所谓速写式的笔线,只是去捕捉人体的这种动态结构的一种方法,疾速使得这些笔线更多地呈现出平直流畅的状态。需要注明的是,此作分别有两个落款,右款“和阗姑娘。一九六二年黄胄于喀什”,为1962年画成落款;左款“一九六二年于喀什喀尔草图,十年浩劫后整理着色,此亦幸存者也。黄胄”,此为后来补款。此补款虽说明了此作后来“整理着色”,但画面本身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平直而劲挺的勾线应基本为其原貌。可以标志黄胄这一画风形成的,还可以在《新疆舞》《黑娜其罕》得到印证。《新疆舞》几乎全是平直劲挺的速写变体线,以此捕捉眼手相应的舞者所凸显出来的腰身扭曲变化,衣纹勾线因此而迅疾平直。同样,《黑娜其罕》几乎完全用平直硬挺的勾线捕捉大形,尤其是为描写黑娜其罕的前倾而画出的由头、颈、肩和背连贯的多条复线,正表明画家把看似矫正体态的多重线条作为其独特的人物画笔墨表现方式。
与《和阗姑娘》《新疆舞》《黑娜其罕》同为新疆写生的还有三幅不同构图的《采风》变体画以及《少女牧驴》《赶集》(20年后补款)和《猎人》等。在这几幅作品里也可以看到,因现场速写需求而增加了用笔的成分,完全以水墨点厾或晕染的部位已较少,竖构图的《采风》的人物与树枝几乎就是他日后最常见的富有弹性的劲挺的线,复线开始较多地出现,甚至《猎人》画中的鹰和马也把本是水墨晕染的部位变为粗笔阔线的运用,这种画鹰、画马的方法在他此后的绘画中获得了更强烈的个性凸显——用大笔快速的挥写替代了温润柔和的湿墨。而从1962年冬延续到1963年的新疆写生,更把黄胄有关女性体态造型的美感捕捉与这种速写用线的融入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如《顶石榴》(1963)画中的少女,以洒脱流畅的线条所融入的墨色,塑造了她正侧面姣美的脸颊和婀娜而挺拔的身姿;再如《军民齐努力》(1962年冬于阿克苏初稿,1963年7月完成于北京)以速写式的大轮廓线捕捉了一站一弯的两位女性形象,近前的塔吉克姑娘与背后解放军女战士形成了神情上的默契与构图上的呼应,其泼辣豪放的笔线已完全具备了黄式人物画的风范。
虽非学院美术教育出身,但黄胄的造型意识却异常敏感,甚至可以说,形成黄胄画风的缘由固然有西北和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深厚积淀,而诉诸绘画语言的则是其对造型形象的敏感性,他比一般画家更深刻地感悟到体态造型本身所独有的绘画叙事性,而不是落脚于那些人物在“做什么”的情节描写上。也因此,他从来就没把速写只作为创作的素材,而是作为绘画的本身,从速写到水墨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语言障碍。这在他早期的《玉龙喀什河边》《春兰》等作品中便可看出,是这些人物丰富的肢体语言承载了黄胄绘画的美感,而速写式的笔墨只是对这些肢体语言的再度创造与发挥。
1962冬完成的《奔腾急》(又名《藏童上学》),应当是黄胄完成其个人艺术变法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此作是黄胄受命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随军采访,在出行前三个小时的间隙直接泼墨挥毫写就的一幅丈二大画。也因是急就章、不容仔细琢磨,其造型的生动、表情的传神、笔墨的飞动均一气呵成,气韵贯通,显现了画家深厚的生活积淀。这幅画作,已完全是其变法后画风的鲜明体现——五位骑马去上学的藏族儿童神态各异,生动鲜活,其人物以速写为基础进行的概括与简化,较丰富地呈现了笔墨的虚实变化,画作均以笔性写出,人物姿态通过平直而富于弹性的复线处理增添了其生动感的表现;尤其是马的描写进一步发展了《猎人》画马的方法,绝去泼绘,全以粗阔的笔线写就,这是黄胄此后画马的基本方法。而“奔腾急”的画名,也是黄胄画风与其绘画精神状态的自我揭示,他追求的就是中国人物画审美中从未表现过的一种动感,而这种动感和他速写线条入画所体现的疾速、跳动、流畅与活泼又是如此的契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黄胄追求的就是一种奔腾的气势、激越的张力。
四、《高原子弟兵》《丰乐图》展示此后驾驭的宏大场景
对于造型的敏感性,也使黄胄比同代画家更懂得人物组合在绘画上的独特意义。的确,黄胄的高明还体现在他比同代大多数画家更能够驾驭多人物形象组合的大型创作上。1962年黄胄创作的不同寻常,还在于他完成变法之际创作的一系列大型绘画上。这不仅仅有《巡逻图》《奔腾急》的创作完成,更有《高原子弟兵》《东海女民兵》《海南女民兵》和《丰乐图》等大型主题性人物画。
《高原子弟兵》以近前六位藏族妇女儿童为高原官兵送茶倒水为主体,辅以中景一位老奶奶为军人倒水,再以远景一字展开的骑兵而使画面形成构图饱满、开阖丰阔的场面。黄胄的多人物组合,并非照片的搬移,而是从人物造型角度对近景主体人物关系的重新设计,它以符合平面构图规律为前提,譬如前景那个一手抱孩子一手端碗喝水的军人被设计为画面正中的主体人物,左侧的母亲与左侧的两个中学生以“密”的布排形成画面左侧众多人群感,右侧那位提水壶的侧身卓玛则仿佛打开了画面右侧令人想象的巨大空间。为了增强画面左侧人群密度感,画家还在这六位主体人物群体之后的左侧,增添了一组老奶奶为战士倒水以及再远的向远方眺望的一组人马。显然,画面的人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但却取得了以一代十的效果。这样主题性的多人物组合,还可以在《东海女民兵》和《海南女民兵》画面上得到印证,并在景色与多人物组合的结合上显现出高超的驾驭能力。
多人物组合不仅涉及人物之间的疏密、虚实、呼应等关系的处理,而且,对中国画而言,最难的还在于如何通过笔墨来把握人与人之间的衔接而使之成为一个整体。1962年再作的《丰乐图》(146×282厘米)是1959年《丰乐图》同尺寸的变体画,多达百余人的巨作无疑是中国人物画史上一幅以焦点透视而展开的大场景群体人物画的经典。这是只有凭借丰富的人物形象积累并能够驾驭大场面的黄胄,才能完成的一幅人物画杰作。该作以维族少女和小伙的双人舞为画面中心,围绕这个双人舞而画了左侧吹、弹、击的乐鼓手以及对面一排密密的观舞人群。此作的难度既有对双人舞蹈生动而精准的描绘,也在于能否画出这么多各具相貌特征、紧凑而不繁乱的观舞人群。男女双人舞的形象抓住了四分之三侧面人体肩颈、腰肢和足踝这几处大关节部位的节奏关系,显现了画家扎实稳健的造型功底;而这两个人又处在围观舞者的人群里,画家以较粗的外轮廓线凸显其主体人物的地位,后面的围观人群则以相对较轻淡而细劲的线条处理,由此产生远近、虚实的空间关系;在后排众多人群处理上,一是以分组形成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疏密有致的群体组合,二是通过着色与着墨的变化形成丰富却不杂乱的整体性。而此作又通过一块巨大的织花地毯不仅统一了画面,而且增添了疆域特有的民族风情气息。
1962年创作的这些大场景的群体人物画,无疑揭示了黄胄艺术风貌的另一特征,他此后创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76,240×180厘米)、《欢腾的草原》(1981,146×366厘米)、《牧马》(1983,210×500厘米)、《叼羊》(1983,64×280厘米)、《听琴图》(1985,96×240厘米)、《草原逐戏》(1986,118.5×370厘米)、《高原初春》(1987,144×278厘米)、《套马》(1987,160×360厘米)、《秋原放牧》(1987,146×367厘米)和《牧马》(1987,143×350厘米)等巨构,莫不以壮阔的场景、深远的透视和生动传神的人畜塑造而成为中国现代人物画的经典。
五、承载黄胄完成艺术变法的一年
1962年对于黄胄来说,的确不同凡响。此年,他完成了自己从《洪荒风雪》到《奔腾急》的艺术变法,此后他的艺术风貌只是在此年完成艺术变法之后的丰富和充实,甚至此年的艺术经历也都是他此后艺术生涯的复制与扩大。
应当为黄胄的1962年做个翔实的纪录:
元旦前夕再作《祖国的眼睛》,后更名《巡逻图》(1)。
元月至6月,继续为《红旗谱》插图创作,赴保定搜集人物素材,并作《春兰》《朱老筑、严志祥、小虎子》《朱老明》《运涛与春兰》《少女牧驴》,在白洋淀画《捕鱼》《河边》,作速写《编席》等。
3月,作《挑担的姑娘》《一曲菱歌》。
4月,为女儿梁缨周岁创作《缨儿》(151×50厘米)、《缨儿》(109×49厘米)。
6月至7月,受命以随军记者身份赴福建边防前线(2),深入边境海岛采访写生,留下了《老榕树》《榕树下》《牧牛》和速写《补网》《准备出海》等画作,并创作大型主题性人物画《东海女民兵》《海南女民兵》。
秋,受命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作随军采访(3)。出行前,在离火车发车前三个小时的间隙创作完成《奔腾急》,又名《藏童上学》。
10月,创作大型主题性人物画《高原子弟兵》。
冬,赴疆采风,先后在阿克苏、喀什噶尔、和田等地写生创作,并作《黑娜其罕》《和阗姑娘》《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舞》《猎人》《采风》等,画速写《缫丝女工》等,直至1963年春。
本年还在1959年初稿基础上,再作大型主题性人物画巨作《丰乐图》。
值得注意的是,此年黄胄创作的描绘家乡与南方的《一曲菱歌》《挑担的姑娘》《老榕树》《榕树下》和《牧牛》等画作,既有生活小景的纪实,也有想象写意的抒情,其笔墨的温润淡雅完全不像描绘新疆人物那样激情四溢、恣肆汪洋,这是否也揭示了成就黄胄人物画变革的对象和地域只被限定在新疆与新疆的民族风情呢。《牧牛》画作上有黄胄自己后来的一段补款,“此一九六二年于厦门所作,当时以景尚可观,保存十余年看来无多少可观处了,说明今天还小有进步”。从画风形成的角度看,这个画中之景的“无多少可观处”,可能更多揭示的还是此景非黄胄风格个性所承载之景罢了。
注 释:
(1)此作创作年代在崔晓东主编《激情燃烧的岁月——黄胄和他的时代》年表中,被标为1963年;在北京画院编《大美寻源——黄胄作品集》年表中,被标为1962年,都同时注明“为国家赠越南胡志明主席”,均为同一作品。原作落款为“一九六二年元旦前夕黄胄写于北京”,现以原作落款时间为准。崔晓东主编《激情燃烧的岁月——黄胄和他的时代》,为炎黄艺术馆、黄胄美术基金会2014年出品;北京画院编《大美寻源——黄胄作品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2)黄胄赴福建边防前线写生时间,北京画院编《大美寻源——黄胄作品集》年表被标为1961年7月底,并记“受命以随军记者的身份,与同道赴福建边防战斗前线,深入边境海岛采访写生四十余天,画了大量表现海防前线军民联防战斗生活的画作。返京后,与同道举办联展。他作的《女民兵》《炊事员》等得到好评”。崔晓东主编《激情燃烧的岁月——黄胄和他的时代》年表则将此事记作1962年,“夏,台湾国民党军来犯。接受赴福建海防采访写生任务。作《女民兵》《炊事员》等多幅速写”。现根据黄胄《老榕树》《榕树下》《牧牛》和速写《补网》《准备出海》等画作中落款,时间应为1962年7月,又《东海女民兵》《海南女民兵》作品落款并无记年,根据《黄胄作品集1943—1966第1卷》两幅作品图注明确的年份为1962年。郑闻慧主编《黄胄作品集》(共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3)黄胄受命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作随军采访的年份,应为1962年秋,因此年中国政府发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崔晓东主编《激情燃烧的岁月——黄胄和他的时代》年表却将此年份误写为1963年3月,该年创作的《奔腾急》《载歌行》和《高原子弟兵》,也都为误写,都应改为1962年(原作落款时间)。而年表中记写的“同年,第四次赴新疆南疆访问写生半年”,也应为1962年黄胄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采访之后。
尚辉,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主编、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