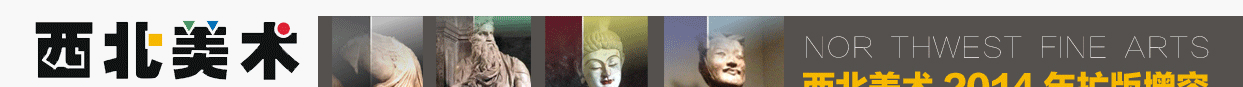高千惠
文化艺术上的“汉唐”是一种盛世形容,而盛世的想象,是源于留下的艺术作品,并非国家的版图大小。想象中的中国长安应该与意大利的罗马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文明见证大城。“长安”与“汉唐”有联结想象;“汉唐”与“中国盛世”亦具联结想象,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往东南迁移后,当代的西北成为科技发展的大后方,其文化发展位置已然边缘化。“长安论坛”与“北京论坛”有着据点意义上的不同。“长安论坛”中的“中国艺术课题”历史文化意义为:有关“本土性”的仰韶文化,如何形成“交流性”的“汉唐文化”,以至于造就出以“人世间”为本、“流动性样态”为美的艺术时期。
中国常言的“汉唐”,在历史时间上相当于西方的中世纪。汉朝(前206—220)与稍晚兴起于欧洲的罗马帝国东西遥立,至今中国人还以汉人为最大族群代表;唐朝(618—907)则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强盛的朝代,至今海外中国城还多称唐人街,然而“汉唐”之间还有混乱的魏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等。从帝国的演变来说,“汉唐”以一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宋代艺术注入了改良的中国文物样态和美学思想。宋、辽、夏、金则以近三百年的时间,又完成第二波南北文化交流。至元、明、清,中国艺术文物还是在不同族裔文化交融色彩中出现风格变化,但因日渐锁国,使文化艺术能量不似“汉唐”那般气势磅礴。此外,就时间而言,“汉唐”之后的中国艺术境地,由实转虚,继起的文人山水世界,逐渐远离了人间烟火。
从汉画的质朴到唐画的典丽,文化艺术上的“汉唐精神”不仅是一种文化开放胸襟的指涉,也是艺术思想上的人间回归。在据点意义上,长安提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文化服务器”般的空间。它如同19世纪的巴黎和20世纪的纽约,都因其包容量与城市机器的运转,而使文化交流达到盛况。许多文献均出现唐代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之细节,留传甚广的唐诗,多出现文武相济、汉胡共处的经济生活情景。在艺术发展意义上,何谓中国艺术上的本土性,在汉唐期间已然是流动状态。汉唐之际的器物、织品纹样之区域性西域风,以及庶民生活的图像记录,虽大异于后起的文人艺术思想,却是思想、文学、诗词、艺术创作最自由旺盛的表现期。
在异国文物和酒肆文学中,如李白《少年行之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醉后赠朱历阳》:“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在《白鼻驹诗》中:“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胡人至大都长安生活,除马鞍酒食文化外,也引进语言和音乐。白居易曾言:“胡啼番语两玲珑。”王建则有“洛阳家家举胡乐。”元稹形容胡曲汉调的流行,写出:“学语胡儿撼玉玲,甘州破里最星星。”针对当时的开放移民政策,孙光宪的《北梦顼言》中曾引崔慎猷语:“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
这种历史上的都会场景,本身既具有文化服务器的功能,提供了联结各种讯息空间,也包容外部与内部的各种机制处境,以达到本土维新之态。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下,艺术世界和政治世界的兴衰不一定成正比关系。例如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佛罗伦萨虽被称为文艺的黄金城,但在现实中,它与南方的罗马教廷争战,也曾面对黑死病的肆虐。政治与经济之外,文化盛世,指的应是一个城市能否扮演“文化服务器”,是否能吸引各地艺术家,或产生出具有能量的艺术家。而这样的生态,有其时空上的契机,也需人本上的致力改善。
近年强调的地域文化复兴论,往往指陈出“文化回归”或“文化盛世”的愿望。如果要用中国最早的“中国性”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中国《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此阐释愿以“声闻于野”与接受“他山之石”的态度,即是一种开放胸襟的“汉唐风范”。
二、迁移,国际风格与地域风格的拉据
从19世纪末至今,中国在面对现代与西方的挑战下,一直在寻找一种“他山之石”,并产生“西学中用”等改革方法,然而,“汉唐文化”精神并非方法论,而是一种文化器度。这样的文化器度,是由一个城市或国度在“文化服务器”角色上的包容量与节控度决定。
长安,曾是北纬35度至40度之间,文化横向交流锦带上的一颗明珠。但当代中国艺术领域,汉唐的长安文化精神之诠释显然有闭锁式与开放式之别。闭锁式之说,把长安和汉唐放在一个“大中国文化”的复兴想象,以政治中国为主体;开放式之说,把长安和汉唐放在一个“中国大文化”的启蒙想象,以文化中国为主体,文化上的“长安”或“汉唐”之产生,乃在于那时候的“中国式大文化”,自信而不排外,同时也不媚外。它没有硬性规定,但有其美学品味上的选择。
在文化和艺术样态的迁移中,北纬35度至40度的天空下,横亘丝稠之路的腰带,也是昔日文化同化最明显的区块。它呈现一种时态的平行观,也是时态交融的结果。以同纬度的欧亚城市作比较。当代北纬40度的大城市有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喀什、北京、汉城等,北纬35度的欧亚大城市有东京、京都、德黑兰、西安、日照、青岛等。在论述欧亚文化交流经验时,这一横带的城市文化,都具有本土性异化与同化的维新现象,也分享了许多文物的相似性。
在近年当代文化艺术展览中,有关这一横带的欧亚文化交流经验,以及面对的议题已出现不同的探讨角度。以下就“2007年卡塞尔文献展”、丝路西段的伊斯坦布尔在当代艺术上的跨欧亚观点,以及以民俗与大众艺术出发的“阴翳礼赞展”中,提出有关这一横向地带的“历史性”“当代性”“地域性”与“全球化”等视觉论坛的种种面向。(1)
(一)“古代性”与“现代性”的样态交流
进入当代,面对“本土性”与“原创性”在形式移民后的改写,所有地域文化都有“古代性”和“现代性”的迁移与再生问题。在当代艺术领域,2007年“卡塞尔文献展”,在强调“现代性”的形式迁移和生存状态下,便以“古代性”相对于“现代性”,以及“现代性过时了吗?”的提问,介入了“形式交流”或“样态挪用”的美学过渡状态。
该展将“现代性”追溯到中世纪至文艺复兴及欧洲发明活版印刷的时期。其立足点,是站在艺术史形式美学的立场上,将曾经在政治、经济、宗教、战乱影响下的艺术样态脉络抽出来。丝路上的艺术文物交流样态,便成了最佳的欧亚文化陆桥样本。当时这个当代大展出现了两个与丝路有关的展览内容。一是卡塞尔的威廉高地宫博物馆,二是卡塞尔市的壁饰博物馆,这两处的收藏品都涉及被消减文化意涵之后的艺术样态。(2)
威廉高地宫博物馆最早期的借展作品,是普鲁士大使戴兹(Heinrich Friedrich von Diez) ,在1786至1790年间,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所购藏的一组波斯、中国、奥斯曼帝国影响下的14世纪至16世纪间之彩绘山水。它们因蒙古军横扫欧亚,以纤细画的形式,加上丝路流传的东方自然样态元素,综合出当时的一种异域风情。16世纪波斯名书法家马扎沙德(Haddshi Mazsud),其1573年的书写亦包括在内。另外具文字和物体陈述的代表,则是16世纪中期一组中国宋、元、明时期的名器图考。它们以图文对照方式,描述器物的形制制造。另一件1662至1722年的清代漆画《百物图》,亦以器物造型和装饰风,显现出文化符码的造像。
在欧洲进入现代启蒙期的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这段历史上的欧亚陆桥,正是文物大融合的花团锦簇期。在伊朗、印度的纤细画和织锦图式中,可以看到龙头凤尾的异鸟、太湖石、几何连环花饰,还有白描的印度民俗画本。民间绘画当中,有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名家葛饰北斋所制绘的《万职图考》,其版刻线条有极限艺术之相。印度甘希(Nabaran Chandra Ghosh)的《市井男女》,是1820至1930年印度加尔各答有名的风俗画类,乃以简易法生动地描绘男女关系。
虽然在作品形式中,仍然可以看到古代性中的现代性与现代性中的古代性,但是以西方观点看待丝绸之路交流艺术,零星选件中呈现出的,多是异国情调般的文化样态。在古代性上,忽略了丝路启站长安的历史位置、汉唐千年间的东西(汉胡)交融关系,也没有涉及更深入的文化生活交流,只作了选样的样态游牧与形式迁移。
(二)丝绸之路西段上的“跨欧亚观”
如果,“2007年卡塞尔文献展”的威廉高地宫作品是来自欧洲观点,那么,同样以欧亚交流地带为讨论的亚洲观点,或是欧亚并存的观点,也自有其文化诠释的角度。当北纬40度抵达东经30度,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乃至其跨着欧亚边界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它的“跨欧亚观点”,乃呈现出一种“国际风”的流转经验,或成为“欧亚同体”的美学形态。
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当代土耳其成为欧盟的一份子。20多年来,“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主题,不论是从历史、文化遗产、当代生活或未来想象,都试图以艺术形式,探讨跨越国家、族群和文化边际的问题。其间,“2005年的第九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伊斯坦布尔”,旨在让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发现伊斯坦布尔的过去历史和现在生活。为了突显城市生活的转变与发展,该展集中在金角湾对岸的贝酉露与嘎拉塔区,以旧有的仓库与公寓大楼为展览空间,并请艺术家驻村,了解和探讨伊斯坦布尔中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状况。
“2001年威尼斯双年展”,土耳其推出以装置、影录、网站打造的《香料花园》,这个主题采自1394至1433年间的一本阿拉伯古籍,在19世纪末被翻成英、法文,内容是以诗性的角度看待人的情欲感官,以及与自然界的关系等情绪世界。因为转译,这本书本身便成为东西方的对话现成物。译本中,西方语文变成主体,阿拉伯原文变成脚注,这个转换(包括转译和转形),遂被视为一种文化交融的表征。进入当代视觉世界领域,《香料花园》所表现的就是东方和西方在后现代情境下,东方对西方承传的排拒,并点出“全球化”与“多元主义”间的矛盾。
“2003年威尼斯双年”,土耳其再度以“伊斯坦布尔”为主题,提出“观看者生命中的24小时”。艺术家瑟兰(Nuri Bilge Ceyla)的影像,为外地人导览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掀开了居民的生活心理空间。其他艺术家,他们用鸟瞰的视线或近景搜索,分别提出伊斯坦布尔居民在两块陆地和一条水之间的生活现实:介于欧亚的人文和地理之处境,以及新旧文化元素之代换。就好像是旧社会的刺青,已成为今日的时尚。
2004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奖”颁给了1961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塔曼(Kutlu? Ataman)。(3)早在“2002年的文献展”,阿塔曼提出的《维诺妮卡·李德的四季》,正是记录保育“孤挺花”品种的李德女士,人与室内盆栽间的一种情感。她以四面屏幕,呈现这个在室内空间伸展出的异国情调。(4)《维诺妮卡·李德的四季》伸展了《香料花园》的理念。善以室内空间为场景的阿塔曼,更藉此提出她的艺术文化观。认为没有中心或边缘之说,每个人的生活就是个体的中心,每个人的自我认同中,都养殖着异色或异国的欲念,并在日常生活里,形成“我”与“他”的共生境况。
“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土耳其推出1970年出生的查拉原(Hussein Chalayan)影录作品《缺席》。其内容同样涉及生物、地理、人类学及环境的认同迷思。“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一直没有固定场所的土耳其馆,终于在威尼斯军火库搭了一个木造屋,上面写着“别抱怨”的英文字,里面有桌椅,观者就像坐在小铺间一般,看着艺术家阿普德金(Huseyin Alptekin)的影录系列《小事件》。其内容包括伊斯坦布尔的拾荒者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城市低下生活者如何乱中有序地经营每日的行为程序。而在“2007年文献展”,土耳其的艾尔汀德(Halil Altindere),拍摄了几个中年男人在挂满五彩毛毯的小木屋里弹唱,当镜头拉开,原来场景是在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建筑的屋顶上,如是呈现出后现代式的空间错置景观。
“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土耳其馆推出《间隔》,作为历史事件随时间的集体诠释而变化之伸述。这些主题趋向显示,土耳其当代艺术的思考结构已然形成。
(三)《阴翳礼赞》中的民俗艺术交流
民俗艺术最易随纬度而流传。针对传统民俗和经典文艺对当代艺术的影响,以及地域艺术家和国际艺术家平台演出之文化主体认同,2009年在爱尔兰、土耳其和希腊巡回展中的“阴翳礼赞展”,则提供了一个从地域演绎出的文化论述之例,而参与的当代艺术名家们亦不讳言其艺术承袭的脉络,与策展单位共同建立了当代影偶艺术的某一支文化论点。
“阴翳礼赞展”,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主办,并与爱尔兰都柏林美术馆和希腊班讷基美术馆共同合作,展题引自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一本论集题目。谷崎润一郎的日本现代生活论集《阴翳礼赞》,感性地描述日本生活空间中幽微的美感和偏执。他的事物影像描述,是带着苗头或迹象的预兆。因此,其“阴翳”也是为某些阴暗角落代言。同样采用《阴翳礼赞》为展览名称,它是以“影子、偶剧、动画”为概念,将跨欧亚与土耳其或希腊有关的当代影偶艺术,作了一个历史文本的爬网。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的策展者,可洛坡(Paolo Colombo)提出,“阴翳礼赞”一词,原是来自南非的肯撒纪2001年在芝加哥当代馆展出时的演讲名称。肯撒纪则自述“阴翳礼赞”正是转用谷崎润一郎(Junichiro Tanizaki)1935年的一篇文章,可洛坡注重的并不是抽象的“阴翳”空间情境,他更在意具象的阴翳,也就是影偶艺术本身的脉络。他仅借用谷崎润一郎的书名,但其理念则提出:从希腊、土耳其出发的影偶艺术之当代表现。
再往前推,此展把影子剧院或谓影偶艺术之源,又归于中国汉武帝因思念李夫人,宫人为之制作皮影,产生如梦如幻的影像归来,以满足汉武帝的想象。影偶艺术或可视为远东的发明,但在今日,印度、东南亚、西亚、北非各地,亦视“偶戏”为其区域民俗文化之一,不仅各有不同的剧本、形式、技法、制作材质,对于源头的陈述,也出现不同的主体论述。
当国际艺术家在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布尔进行文化对话时,我们看到国际风格和区域风格的拉据。引经据典,成为一种知识背景,未必是文化表态。同样以影偶艺术为主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的“阴翳礼赞”,与东北亚当代动漫玩偶艺术的发展已然形成两条路线。但从汉武帝的皮影戏之典故出发,属于西亚的伊斯坦布尔“阴翳礼赞展”,对于东亚文化也释出知识上的联结手势。
三、东—西,欧亚陆桥上柔性的并行线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在远东、中亚、中东、西亚的当代对话中,长安有不亚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据点意义。在“中国性”的探讨中,长安与西域的关系,汉唐长达千年的汉胡文化交融经验,均见证了文明、文化、文物在闭锁空间内无法前进。东—西,对欧亚陆桥这一平行纬度来说,是柔性的并行线。东西方艺术的相互影响,已打破政治性的地理圈限。
汉唐之后,中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来自东南沿岸,但在国家意识下,西方成为一个敌对的对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和上海成为新的国际文化交易都会,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市场经济蓬勃期,虽与西方艺坛交流频繁,收藏买卖热络,但所发展的新现实主义,尚未产生一种具交流性或影响性的美学样态。当代(中国)艺术中的“中国性”,少了汉的质朴与唐的典雅,也少了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能在战乱频仍中创造最庄严美丽的佛像(宗教精神)能力。
当代(中国)艺术中的“中国性”究竟怎么了?有论者认为存在,有论者认为不存在。(5)尽管各地域生态不同,当代艺术经常还是国际风格与地域风格的拉据战场。古代性与现代性、历史性与当代性、地域性与全球性,未必都是对立的。在当代跨文化展览的意义,便是从这些对立面中寻找跨时空的联结,或是在没有被发现的余韵中,看到文化的可沟通性与精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