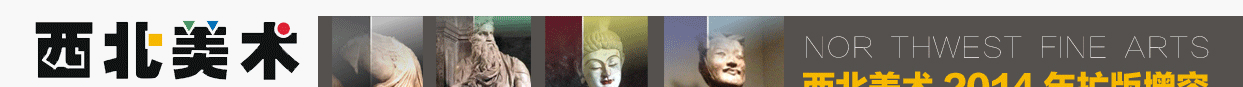沈奇
摘要:“上游美学”理念,系在笔者多年的美学思考基础上,经由西部诗歌在内的现代汉诗研究、西部美术理论研究和当代书画研究,逐步引发梳理出的一个新的学术理念。在与程征、张渝共同策划并出任学术主持,为陕西美术博物馆连续成功举办三届“高原·高原——中国西部美术展”,也为“上游美学”的理论思路增加了新的考量。有关“上游美学”理念和当代艺术实践相互认证与阐释后,大体厘清了思路并确定文意导引。
关键词:“上游美学”;诗意;自若;原粹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本论文题目与四个关键词:其实构成了正题与副题两部分。“上游美学”与“诗意”“自若”“原粹”互为关联,由此构成一个“家族谱系”,并最终归旨“上游美学”这一核心理念的确立之论证。四个关键词相互阐释与认证后,有关“上游美学”的理念,大体也就清楚了。
诗意
诗性汉语,诗意中国,这是认识中华文明与传统美学的根本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来自这个民族最初的语言;他们是怎样“命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便怎样“命名”了他们。尤其是现代人,大体已是“语言的存在”遭遇怎样的“语言编码程序”,便以怎样的程序方式认知世界,同世界交流。包括作为“语言中的语言”的各类艺术创作与艺术活动,也离不开所处“语境”及受此语境“编程”下的“心境”制约,形成不同的艺术感知方式和不同的艺术表意方式。由此可以推断,在不同母语中生成的艺术家,即或使用同样的艺术材质,选取同样的艺术形式,其生成的文本,也必然是有内在差异的。
中华自古有诗国之称,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诗与生活的关系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密切。孔子说“不知诗无以言”,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汉语的“诗意运思”(李泽厚语),由此与西方拼音语系之“理性运思”分道扬镳,形成两种文明形态、文化谱系及不同的艺术道路。
对此,笔者自创“味其道”与“理其道”的重新命名,来概括汉字文化与拼音文化对世界不同的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之根本属性。
“味其道”中的“味”,作动词用,即“诗意地”去感知与表意。中国人早知天意,明白“道”原本不可解,故止于“味其道”,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里的“不可言传”不仅指万物之道原本就说不清楚、讲不明白,而且暗含最好不要说清楚、讲明白的意思。小者,说清楚讲明白就“没意思”了;大者,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1),故而认领“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道德经》),并了然“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故,中华文化以及整个汉字文化谱系中,向来“诗”大于“思”。
由此,面对天、地、人、神,中国古典汉语中的智者、诗者、艺者,及一切“微言大义”者,出口或下笔之前,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说明白或无法说明白的是什么,而后深怀敬畏之心,试着说一说。其背后深层的立场在于:世界是不可言明、不可通约、不可量化的。故汉语之于世界、之于人生,多以在“味其道”而自得而适;“道”以“味”显,有“味”则“乐”,“乐以道和”(《庄子·天下篇》)道以乐施。
“文章千古事”,味其道也!“味”是对世界的体味或体味后的说法,“道”是世界的原在。
汉语“味其道”之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的根源在于:汉字及汉语的诗性本质与非逻辑结构。汉字以形会形,意会而后言传,传也是传个大概,“恍兮惚兮,其中有道”。(《老子·道德经》)故,汉字之于汉语,具有不可穷尽的随机、随缘、随心、随意之偶合性,因而对“万物之道”的“识”与“解”,亦即其感知方式与表意方式,也大多是“意会”性的,直觉感悟,混沌把握,不依赖于理性思维及逻辑结构的链接。所谓“大而化之”“知其白守其黑”,由“悟境”入自“悬疑”出,而“道法自然”“与造物者游”《庄子·天下篇》),归旨于“或”的非此也非彼 (止于“or”而非“yes or no”),守“魅”以“隐在”。正是在这一个“魅”字和这一个“隐”字中,古典汉语诗性和诗意中国的“基因密码”得以传承发扬而生生不息。
我们知道,整个西方近现代的文化发展与文明进程,说到底,是在“科学进化论”与“历史必然性”及“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由无所“禁忌”而全面“解密”以改造世界,以及自传统“仪式”化语境向现代“游戏”化语境全面转换而致全面“祛魅”的过程。按照张志扬的说法,即走了一条“神被人剥夺——人被人剥夺——人被物剥夺”的“轮回”之路。(2)由此,世界不再“隐秘”,天下“大白”,而“诗意”随之消解——现代汉语语系与现代西语语系共同遭遇的诗与思之现代性危机,于此而生。
当代汉语诗人、作家于坚,曾给诗歌下过别有意味的定义,说诗是“为世界文身”。“文”同“纹”“文,画也”(《说文解字》),“集众彩以成锦绣,集众字以成辞意,如文绣然”(《释名》)。可见,“为世界文身”的功能不在改造世界,而在礼遇世界、雅化世界——这是反思百年中国“新文学”“新美术”以及其他“新”什么的一个大前提。
现代汉语语境下的百年中国之诗与思,是一次对汉语诗性本质一再偏离的运动过程。所谓中华文明的根本,尤其是我们常拿来做“家底”亮出的传统文化中的诸般精粹,说到底,是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和诗性人生风采的广大——既内在又张扬、既飘逸又宏阔、元一自丰而无可俯就的精神气度,至今依然是华夏文明的制高点。而这个根本与精神得以孕育与生长的基因,在于汉语的诗性本质。因而,如何在急功近利的“西学东渐”百年偏离之后,重新认领汉字文化之诗意运思与中华艺术之诗性底蕴,并予以现代重构,大概是首当其冲需要直面应对的大命题。
自若
包括所谓“文化人”以及“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当代中国人,仅就精神气息而言,比之包括“现代”“后现代”乃至一些“前现代”国家之人,到底差别在哪?可以说,只“自若”一词,立判分明。
或可由此虚构一个“行为艺术”——随机抽样拍摄一百个国家各一百幅街头行人肖像,然后比比看,自会发现,“自若”的缺失,在当代国人这里是多么明显和严重。假若再将这样的拍摄对比,限定在所谓“文化人”范围内,其“惨状”更是可想而知。
无论文本还是人本,无论“庙堂”“民间”、还是“在路上”,虚于“自若”而只在“顾盼”,以致“自信”无着,早已成百年国族一大痼疾。作为常识,我们知道,所谓“庄玄境界”,所谓“魏晋风骨”,所谓“汉唐精神”,所谓“天机舒卷,意境自深”(3)等等,其核心所在,无不与主体精神之“自若”相关。“自若”既失,方方面面的堕退,皆成必然。近年学界热议的中华“文化身份”之重新确立问题,实质也在这里。
说“自若”,先得说与“自若”相关的其他几个和“自”有关的词,如“自由”“自在”“自得”“自然”等,以作佐证。西人有言:人生而自由。这话反过来理解,实际上是在提醒:人生而不自由;正因为不自由,才老想着要去争那个自由。其实争也没用,人类发明文化,推进文明,说到底就是要将天下的人和事归类分层以求好管理,及至现代,更是通过各种空前进步空前科学的手段,将所有身心本不一样的个人,硬生生归拢成体制化及时尚化的类的平均数,没了个性,还谈何自由?
便有艺术家们站了出来,要坚持争那个自由,称艺术创造为挣脱社会枷锁的“获救之途”,大有“舍我者谁?”的架势,为此一二百年来趋之若鹜者如过江之鲫,前仆后继而蔚为壮观。可观到最后,也大多只是造了些形势、观念、运动和有关艺术家们的故事而已,没见为现代人带来多少“自由之路”可去走。这还说得是西方,再要看当代国人,就更不堪了。
自由方得自在。也只有自在的人才有权谈论艺术或从事艺术。艺者“异”也。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发为神游于物外,显为个在于群上,乃“异”而艺。这个“异”,就是个我的自在。艺术的功用,无论在艺术家那里还是在艺术欣赏者那里,都是为着跳脱各种体制性话语的拘押与束缚,由类的平均数回返本初自我的个性空间,得一时之精神自由和心灵自在。
因此在常人眼里,诗人和艺术家总是有些“另类”,乃至视为“异族”。其实到了当代,这样的“异族”也大多有其“异”表,无其真自在。真自在的人贵有“心斋”,不为时风所动,亦不为功利所惑,而得大自在;有大自在之心性,方通存在之深呼吸。艺术家更得是如此,先修练就一个独立自在的“心斋”来养就独立自在的笔墨,才可进一步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求创造。特别是中国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本来就是既生于境又生于心的物事,更是古代文人隐修独善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今,却大都成了获取名利的角逐,无不充满了功利的张望和虚构的荣誉。一时成功者遂虚骄傲慢,一时未成功者则虚张声势,总是心有旁骛而难得自在,那笔墨中也便难免虚浮造作之气了,所谓心境既乱而风骨不存,一切皆无从谈起。
以“自得”作中国文学艺术精神之灵魂观,是笔者近年小小的一个新领悟,且以为,现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的迷失与破败,皆与失去了这一“关键词”的内涵有关。想来古人写诗作画,无论是“直言取道”还是“曲意洗心”,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起根发芽,都先是打自个儿得意而生的,没有一个预设的“服务对象”或“展示平台”来提醒你该如何写、怎样画,以及“创新” “探索”“笔墨当随时代”诸如此类的“闹心”话题生干扰。即或有知己相投,那也只是三两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无涉“运动”,更鼓噪不了“潮流”的。这是就其艺术发生而言,从“接受美学”说,也只是各随所好,各取所爱,个人乐意之事,仍属于“自得”。现代以降,问题来了,大凡文学与艺术,无论发生还是接受,一律拉着时代的手,跟着潮流走,从“启蒙”到“宣传”再到“市场”与“时尚”,一路折腾过来,越来越背离了艺术的本质,无“自得”之自在了。大家都活在当下,活在虚构的荣誉与表面的繁荣中,而纷纷陷入角色化的“徒劳的表演”(陈丹青语)。即或也能折腾出形式的创新或风格的转场,但到底心魂已失,难以深入时间而作经典之传承。
而自在的人一切自然,过日子自然,搞艺术也自然。“自然者为大美”,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中向来讲这个理。这理无异于天理:你看天公造物,即或是石子小草也难找出一模一样的,各自自在生色,感动人情。只有人会造些不感人的东西,譬如砖头(以及地板砖等),制作得再精致,也不可审美,因为它不自然。
我写过一段现代诗话:诗要自然,如万物之生长,不可规划;诗要自然,如生命之生成,不可模仿。自发,自在,自为,自由,自我定义,自行其是,自己作自己的主人,自己作自己的情人——然后,自得其所。一切艺术,但能进入这样的一种境界,总能出好东西;或许才情所限、遭际所困,不能企及经典,却也不失真品质,无涉伪艺术。艺术是文化心态的外化。从文化心态来说,古人讲究要归于“淡”(淡泊明志),归于“简”(生事简而心事素),归于“自然”(自然生成,不强刻意)。现今中国文学艺术家们,总是妄念太多,无论是沉溺于技法,还是偏执于观念,都充满了功利的张望,难得自然生发,或能张扬点外在的美,到底不能持久感人。
由“自由之思想”,到“自在”之精神,由“自得”之心境,到“自然”之语境,合为“自若”,方得以“形神和畅”——这是中国艺术精神的要义。
一切艺术作品,都有“显文本”和“潜文本”两种文意,合成为审美价值体现。“显文本”是题材、样式等外在的东西;“潜文本”是语言、人格、精神气息,即作品的内涵。在正常文化生态下,二者是水乳交融而并体显现的,没有形神分离的问题。我们赏读古代经典文学艺术作品,常常感念于心的正在于此:心手相宜,形神和畅。但今天的时代语境大不一样,诸如“意识形态机制”“展览机制”“市场机制”“时尚机制”等强制下的生态所迫,艺术家们常常要屈从其主导和驱使,这时候,能否在“显文本”下有机地保留“潜文本”亦即人格与语言的个性魅力,就成为其作品能否超越时代局限性的关键。
我们常说“笔墨要随时代新”,也常说要“超越时代局限”,但如何“新”,怎样“超越”,并不十分明确。其实作为“显文本”的题材、样式等外在的东西,不管是束缚还是解放都不重要,因为所有的“时代”都是有局限性的,能超越的只是“潜文本”,即你的人格和语言的修为。只有“潜文本”的有机存在,才能将有局限的“时代性”转换为可深入时间和历史更深处的“时代性”。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如古人那样“心手相宜”“形神和畅”。当然,今人无法做古人,必须进入现代语境,表现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在现代性的诉求与传统艺术本质的发扬之间,寻找到一些可融合的相切点,提供新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生活体验和语言体验及其表现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显文本”与“潜文本”的背离或分裂现象的借口,我们在好的、优秀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依然不难发现那种“形神和畅”的精神品质,也依然是需要我们为之进取的精神境界。
说到底,所谓“自若”,一言而蔽之:无论做人、做学问还是从事文学艺术,有个“原粹”灿烂的自己!
原粹
“自若”是精神层面的“原粹”——保持清晨出发时的清纯气息,那一种未有名目而只存爱意与诗意的志气满满、兴致勃勃,从而得以“脱势”而“就道”,“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4)。
当代学术产业化、艺术市场化后,一切学问,一众文学艺术家,总难免刚刚开始种庄稼,就已经盘算着“柴火”的多少,遂将古人前人的“见贤思齐”转换为“见先思齐”,争着当下之“出位”,难得“修远”以沉着,话语盛宴的背后,是情怀的缺失、价值的虚位和主体精神的无所适从,以致成为当代学术语境和艺术语境的“暗疾”而不治。
实际上,由“宣传”而“市场”,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尤其是美术创作,大都由“自得”而转为“经营”了——本来是艺术家之主体精神与艺术语言、艺术文本之间的“自我对话”(此为艺术创作的原初推动力),现在变成了艺术家携带“预谋”与“心机”的一种与“市场之神”与“展览之主”之间的对话,所谓“他者”性的对话。
如此伤神阻意之心理机制压迫下,岂能有真情实意为存在写真、为历史树碑、为灵魂存照、为丹青写精神?
实则,一切学术成就和艺术成就的背后,必有其相应的学术精神和艺术精神作支撑;一切学术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背后,也必有其学术人格和艺术人格作支撑。今日为学问为艺术者,真要想脱出“形势”、潜沉于“道”以求卓然独成,无非三点:立诚、笃静、自若。亦即守志不移,静心不变,定于内而淡于外,于朝市之繁嚣中立定脚跟,“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而得大自在——身处今天的时代,让艺术气息和艺术语言亦即人本与文本都能回归单纯、回归自得,不但已成为一种理想,甚至更是一种考验:平庸或超凡,端看是否过得了这一关。
这是“上游美学”的精神源头。
还有语言层面的“原粹”,即找回“本该如是”的“基点”;先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再说我们到哪里去的问题。
以唯现代为是的断裂方式,和唯新(以及“革命”)是问的运动态势,持续百年的“新文化”“新文学”“新美术”之后,在世界地缘文化格局中,作为中国文化指纹之所在的诗、书、画及其它文学艺术,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西学不如“洋人”,中学不如“古人”,枉道以从势(孟子),唯“势”昌焉,而“原道”隐遁;当年跨涉两条长河“尝试”(胡适)与“呐喊”(鲁迅)的“新”,如今大体上只剩下西方现代化一条河流边的徘徊,以及“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纠结与焦虑,或许还有莫名的“郁闷”中那一缕“藕断丝连”的“乡愁”……
这样的一种客观认知,大概不会有多少异议。而我们知道:一个时代之诗与思的归旨与功用,不在于其能量即“势”的大小,而在于其方向即“道”的通合。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过于信任和单纯依赖主导百年的“现代汉语”之“编码程序”,及由此导致的汉语诗性三度“降解”之弊端——
借用西方句法、语法、文法改造而“来”(“拿来”“舶来”)的现代汉语,比之以字词思维为主的古典汉语,其“诗意运思”之本源属性,先就降解了一层(当然,其“理性运思”的属性也随之上升了一层);再用这样降解后的现代汉语,去翻译西方的经典之原典·元典,并且到后来还得翻译汉语自身的古代经典之原典·元典,其“原典”“原道”的“原汁原味”及“原义”“原意”,难免又降解一次(语义还原的难度之外,更有语境还原的更大难度)。
再拿这经由两次降解后的“思想启蒙”之思与诗,来言说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其结果,只能导致第三次降解。
诚然,百年来我们一直在鼓吹要中西兼顾之“两源潜沉”,但终归抵不过现代汉语的“三度降解”而致两源皆隔。即或因自信所失而急功近利唯西方一源为是,其实打根上也从来就没有可能真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你一直就无法真确明晰地认知到,原本的“蓝”到底为何!于是只能是西学不如“洋人”,中学不如“古人”——如此两源无着,后来者更只有随波逐流而“与时俱进”的份了。
事实上,所谓“新诗”,所谓“新美术”,所谓“当代艺术”,以及等等,百年革故鼎新,一路走来,无一不面临或“洋门出洋腔”的被动与尴尬,或既不“民族”也不“世界”而“两边不靠”的身份危机。是以可想而知,越到后来,尤其当代,即或真有些许个在的“创新”,也大多属于模仿性的创新或创新性的模仿,难得真正原创而独成格局。这样说不是要重新回到古典的之乎者也,而是说要有所来之处的古典素养作“底背”,才能“现代汉语”出不失汉语基因与风采的汉语之现代。作为另一个常识,我们也知道,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所谓大师,无一不是立于传统的基础而又能保持自由呼吸的人,而绝非只活在当下者。
由此显而易见的是,一个造山运动般的大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告别“革命之重”,我们无可选择地“被”进入到“自由之轻”和“平面化游走”的困惑境地而无所适从;不是自由的行走——脚下有路,心中有数,有来路,也有去路,而是碎片化的自由漂流——无来路,也无去路,只是当下感应,即时消费。正如作家韩少功所指出的:我们的文化正在进入一个“无深度”“无高度”“无核心”及“没有方向”感的“扁平时代”,“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并在一种空前的文化消费语境中,在获得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反而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5)
语言的“先天不足”,精神的“后天不良”,百年急剧“现代化”的“与时俱进”,驱使我们终于走到这样一个“关口”——如何以现代中国学人和文学艺术家的眼光,去寻找传统文化中的“原粹”基因,并在现代生存体验、现代生命体验和现代语言体验的转换中,寻求与诗性汉语和诗意中华之“原粹”基因既可化约又焕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故,“梦回大唐”也好,回溯“汉唐精神”也好,以及“新儒学”“新古典”等等诸如此类的时兴倡导,其立足点,其归旨处,都该当是要汲古润今、借古证今而以利未来的。
这里所谓汲古润今的“润”,是要汲取传统精粹中的诗性生命意识,来作为当下物质时代的精神植被,以润国魂;这里的“证”,是要借体现在诸如“汉唐雄风”以及“魏晋风骨”中超凡脱俗的主体精神,来对质当下的追名逐利蝇营狗苟,以证人格。如此,方能由“枉道以从势”(孟子语),返身“大道”“原道”,而正脉有承!同时,这样的“正脉有承”,落实于每一个个体,尤其是活跃于当代话语场中的各种某某“家”们时,有一个需要再三提醒的心理机制要点,即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艺术(一切的“诗”与“思”)的存在,并非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擢拔”自我,而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礼遇”自我——从自身出发,从血液的呼唤和真实的人格出发,超越社会设置的虚假身份和虚假游戏,从外部的人回到生命内在的奇迹,平静下来,做孤寂而又沉着的人,坚守且不断深入,承担的勇气,承受的意志,守住爱心,守住超脱,守住纯正,以及……从容的启示。
而作为“物质暗夜”(海德格尔语)中的“脚前灯”,在一个意义匮乏和信仰危机的时代里,真正的学问,真正的文学艺术,更要有重新担当起对意义和信仰的深度追问与叩寻的责任:包括对历史的深度反思,对现实的深度审视,对未来的深度探寻等,并以此重建生命理想和信仰维度,也并以此重返“诗意”“自若”“原粹”的“上游”之境。
结语:所谓“上游美学”
水,总是在水流的上游活着。
作为汉语“诗”与“思”的“上游”之所在,一是已然典律化的、历时性的、可重新认领的“上游”,如上文所提及之“汉唐精神”等;二是潜隐于当下的、共时性的、需重新探究的“上游”——此即“上游美学”之新理念的出发点。
“上游”——生命的初稿,青春与梦想出发的地方——初恋的真诚,诺言的郑重,纯粹、清澈、磊落、独立、自由、虔敬……还有健康,尤其是心理的健康,只有健康的“诗”者与“思”者,才得以“自若”,才得以“原粹”粲然而净空生辉,也才足以在沉入历史的深处时,仍能发出自信而优雅的微笑。
从“上游”出发的“诗”与“思”,是回返本质所在的选择:既是源于生活与生命的创造,又是生活与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
回溯“上游”的“诗”者与“思”者,只是仅仅乐意为“诗”与“思”而活着,绝不希求由此而“活”出些别的什么。
亦即,真正的“上游”之“诗”与“思”,不仅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言说,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仪式——
远离喧嚣浮夸和妄自尊大的时代主潮,远离闭门造车式的昏热想象和唯功利是问的刻意造作,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的投影与复制;消解功利性,消解娱乐化,消解平庸化,并重新学会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生活中一切卑微而单纯的事物,将所谓雄强进取之势转而为恬淡自适的生命形式,深沉静默地与天地精神共往来,不再有身外的牵绊,只在生命诗意与笔墨寄寓的和谐专纯,而乐于咫尺之间一臂之内挥洒个在的心声。
回溯“上游”,再回望“下游”,自会发现那是怎样的一种不堪——
无中心,也无边界;无所不至的话语狂欢,几乎荡平了当下生命体验与生存体验的每一片土地,造成整个诗性艺术背景的枯竭和诗性艺术视野的困乏。看似新人辈出,且大都出手不凡,却总是难免类的平均化的化约;好作品不少,甚至普遍的好,却又总觉得带着一点平庸的好——且热闹,且繁荣,且自我狂欢并弥漫着近似表演的气息,乃至与其所处的时代不谋而合,从而再次将个人话语与民间话语重新纳入体制化(话语体制)了的共识性语境。
而我们知道:个人的公共化只能反而导致个人的消失。
其根源在于:与自然的背离,与自我的背离,与自由的背离。这是所谓“现代化崛起”的必然结果。
但社会不是统一的,且分裂的各个不同领域有着不同发展模式。丹尼尔·贝尔便曾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分成三个服从于不同轴心原则的“特殊领域”:经济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经济与技术领域“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中含义是进步”。而文化领域则不同,它无所谓“进步”,却“始终有一种回跃,不断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所以社会呈现出“经济与文化复合体系”,且经济和文化并“没有相互锁合的必要”。因此,对于经济与技术一味的“现代化”进步要求,文化总会适时地“回跃”。(6)
由此导引出“上游美学”的“回跃”功能:在失去季节的日子里,创化另一种季节;在失去自然的时代里,创化另一种自然;在解密后的现代喧嚣中,找回古歌中的天地之心;在游戏化的语言狂欢中,找回仪式化的诗意之光——再由此找回:我们在所谓的成熟中,走失了的某些东西;我们在急剧的现代化中,丢失了的某些东西;我们在物质时代的挤压中,流失了的某些东西——执意地“找回”,并“不合时宜”地奉送给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去等待时间而非时代的认领。
“艺术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7)
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的生命体验,原创性的语言体验——这是“上游美学”的核心理念;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再造传统——这是“上游美学”的基本理路。
至此,两脉“上游”汇合为一,其共同的气质与风骨便是本文关键词之“诗意”与“自若”,并最终归旨于本文另一关键词“原粹”——原粹粲然,元一自丰,而原道复归——由此,在溯流而上的生命“初稿”中,在作为最初的旅行者的足迹中,找回复生的诗意,和“还乡”的可能。
注 释: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页。
(3)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版,“三版自序”文页。
(4) 转引自陈丹青:《1989——1994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6页。
(5) 韩少功:《扁平时代的写作》,《文艺报》2010年1月20日版。
(6)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6-60页。
(7) 转引自让·克莱尔:《论美术的现状——现代性之批判》(河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作者简介:沈奇(1950— )男,诗人,文艺评论家,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