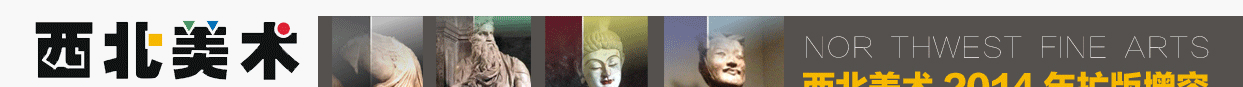摘要:本文主要阐述汉斯·贝尔廷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当代艺术是一种全球艺术。原因在于,当代艺术是西方的艺术概念向全球扩展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贝尔廷认为,艺术和艺术史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艺术作为一种西方观念是以排斥手工艺、大众文化和非西方艺术为前提的。但是在“二战”以后,不仅非西方的艺术创作需要获得承认,西方内部也分裂成了欧洲和美国两大阵营,无法维持一个统一的艺术概念。同时,以否定传统为宗旨的现代主义也反过来变成了一种历史和遗产,因此走向了终结。当代艺术在媒介和时间观念上都突破了现代主义,因此难以纳入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艺术史。
关键词: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当代艺术;全球艺术;媒介
一、现代主义的终结
从贝尔廷和丹托的情况来看,艺术或艺术史的终结是和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艺术的终结》中,丹托有关艺术之终结的解释,主要建立在再现论和表现论这两种范式的基础上。他认为,再现论实际上已经隐含着艺术的终结这一观念。因为,如果把艺术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描摹,看作是一个不断接近视觉真实的技术发展过程的话,那么一旦在技术手段上达到了对视觉真实的准确再现,艺术的历史也就完成了。另一方面,从表现论的角度看,由于艺术只是主观情感的表现,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历史可言。进而,丹托遵照黑格尔的方式,认为当艺术脱离感性因素,变成对艺术概念的反思时,艺术也就走向了终结,变成了哲学。(1)
这一解释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现代主义的因素,只是丹托没有突出这一点。在1997年的《艺术的终结之后》中,当丹托再次对艺术的终结进行解释时,现代主义就变得非常醒目了。他所说的现代主义主要是格林伯格意义上的,也即对艺术自身的反思。按照丹托的说法,“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标志着一个点,在它之前,画家是按照世界自身呈现出来的样子来再现世界的,描绘人物、风景和历史事件犹如它们出现在人眼前。而现代主义则把再现的条件本身当作中心,因此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它自己的主题。”(2)
丹托原来的解释之所以涉及现代主义,是因为对艺术的反思可以看作是一种现代主义态度。这正是《艺术的终结之后》大力发展的主题之一。当然,丹托面对的依然是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按照先前的解释,这件作品之所以标志着艺术的终结,是因为它提出的不再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即什么是艺术。新的解释把《布里洛盒子》跟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观念联系了起来。丹托说,格林伯格根据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试图把绘画跟绘画之外的东西区别开来,强调绘画的“媒介”和“纯粹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由于绘画就是材料,因此无法把一幅画跟纯粹的墙壁区分开来。这正是《布里洛盒子》的情形。所以,“当格林伯格认识到艺术作品与纯粹真实的物品无法在视觉上区分这一两难困境时,当需要站在意义美学的角度强制性地取消一种物质主义美学时,现代主义就走到了终点。”(3)
在丹托看来,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观念实际已经隐含了艺术的终结这一结论。原因是,如果说现代主义绘画的本质是纯粹的媒介,那么艺术达到这种本质之日,也就是它终结之时。推而广之,任何设想艺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人,都必须承认它是会终结的。在丹托这里,终结涉及的不仅仅是艺术,而是作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整个历史。按丹托的说法,科学和哲学也同样会走向终结。
当丹托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艺术的终结时,他跟汉斯·贝尔廷之间的距离也在拉近。在贝尔廷看来,艺术和艺术史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并不是自古就有。(4)具体说,艺术是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或知识体系。因此,无论是艺术还是艺术史,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现代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主义把艺术看作是风格的线性演变和进步。贝尔廷指出,李格尔1893年发表的著作,题目就叫《风格问题》。沃尔夫林出版于1915年的《艺术史的基本概念》,副标题是“近期艺术的风格发展问题”(Das Problem der Stilentwicklung in neueren Kunst)。因此,尽管这些早期的艺术史家都拒绝研究他们同时代的艺术,即现代艺术,但他们秉承的观念跟现代艺术家没有区别,都是只关心艺术的形式或风格。贝尔廷甚至认为,艺术史就是由“历史”这一概念扩展到“风格”这一概念而形成的。因而,人们可以从这一对概念中辨认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面相”(5)。那些开始将目光投向现代艺术的艺术史学家,如迈耶-格雷夫(Julius Meier-Graefe)等,声称老大师的艺术首先就是一种“风格”,而且这种风格的“历史”也延续到了现代艺术之中。贝尔廷认为,这些研究现代艺术的艺术史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即维护艺术史的内在统一性,而不管新艺术与旧艺术之间的差异。
其次,“风格”在现代主义艺术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普遍概念,于是个体和文化特殊性,都变成了否定的对象。就此而言,贝尔廷认为,“早期艺术史的方案和现代性的方案以一种顽固而又几乎是悖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6)。因为那些面向未来的艺术和政治运动都是在一种乌托邦理想的激励下进行的。未来主义、达达派和风格派都体现了这种理想。从未来主义的口号看,“……‘历史’总是用来对抗可恶的‘传统’,‘技术’要用来取代人性化的‘文化’,而从集体产生又作用于集体的新‘风格’,则应该代替资产阶级时代的‘人’和‘个体’”。(7)1918年,风格派在其《宣言》中提出,应该阻止甚至消灭“个体的统治地位”,使“普遍性”获得胜利。用贝尔廷的话说,在未来主义和风格派关于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中,“不管代价如何,‘历史’必须重新开始,以帮助普遍性的、人不再在其中起作用的‘风格’获得胜利”(8)。1921年,达达主义者豪斯曼(Raoul Hausmann)创作了一件作品,叫做“机械头颅”,其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精神”。他后来解释说,“人们没有什么特征;他们的脸不过是理发师弄出来的图像而已”(9) 。(图1)
就艺术史来说,随着现代主义观念的出现,艺术家和他们的生平就不再是主要的关注对象了。“‘风格’是作为个人的对立面来构想的,象征着纯粹和普遍的知觉,这种知觉看起来跟任何特定的文化传统都没有关系。”(10)艺术创作中的“抽象”跟艺术史研究中的“形式分析”相为表里,因为它们都只涉及形式和色彩,而不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在现代主义早期,艺术家和艺术史家都在追求一种“纯粹性”,对艺术史家来说,艺术有一部“内在”的历史,它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则展开,艺术史家的任务是将这种规则揭示出来;而艺术家则认为他们自己的任务是最终达到一种“客观和普遍的艺术”。因此可以说,“艺术史家和艺术家的做法相同,都是以一种集体性的现代主义理想为己任”(11)。
再次,这种关于风格线性进步的观念,当用来理解同时代的艺术创作时,就表现为“前卫”。关于现代主义、前卫及其与艺术史之间的关系,贝尔廷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中有过阐释,他后来在《全球时代的当代艺术与博物馆》一文中总结说,“现代主义艺术最好被描述为一种反映了线性进步、征服和创新观念的前卫艺术,这也证明了它是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不受欢迎的过去来反对的。我们应该明白前卫最初是一个军事术语,正是它使得在艺术语境中来衡量进步和创新成为可能。因此就需要艺术史,而艺术史相应地又需要艺术博物馆来展示其材料和成果。”(12)
然而,按照贝尔廷的分析,现代主义确立的线性进步、普遍主义、不断创新等原则,在当代条件下都失效了。首先,当代艺术不再遵循风格的先后更替这一逻辑。用丹托的话来说,在当代艺术中,根本就没有“风格”这种东西。其次,作为现代主义核心概念甚至同义语的“前卫”,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向社会生活的渗透,前卫和现代主义曾经极力反对、否定和压制的那些东西,如个体、传统、文化特殊性乃至市民文化等,都变得岌岌可危,变成了需要拯救和保护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反传统已没有太大意义。另一方面,前卫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当不断创新成为现代艺术的基本信条时,创新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传统。前卫艺术原本是通过反传统来对抗大众的庸俗趣味,但如果它自身也成为了一种传统的话,那么它所反对的东西可能就不复存在,其对抗也可能会沦为一种空洞的姿势:现代主义或前卫本身作为传统留下来的已经是全新的东西,继续创新似乎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在贝尔廷看来,现代主义观念是艺术史写作和艺术创作的共同基础。例如,对“风格”或“纯形式”的关注,既是现代艺术创作的基本信条,也是维持艺术史内在统一性的前提条件。从这一角度看,现代主义原则的失效,必然会导致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危机,即由于当代艺术不再遵循现代主义的原则,因而也无法用原来那种基于现代主义观念的方式来书写。进一步导致的结果是,由于无法将当代艺术纳入到原来的艺术史框架,整个艺术史也无法维持自身的统一。
二、全球艺术与世界艺术
在贝尔廷看来,由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艺术史的终结也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性遇到了边界。这里首当其冲的是隐含在现代主义中普遍主义观念。由于现代主义是从19世纪的欧洲产生的,在当时设想一种普遍、统一的艺术是可能的。但是“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普遍性的艺术概念也面临着挑战。这种对于普遍主义的质疑,跟丹托有些相似。丹托认为,现代主义在艺术中的表现之一,是通过宣言来提倡某一种艺术观念,并且认为其他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式都是“错误”的。因此,他认为现代主义具有“极权主义”和“独断论”的色彩,跟当代艺术中的多元主义格格不入。
跟丹托不同的是,贝尔廷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现代主义的。在他看来,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欧洲的文化现象。人们凭借“现代”这种观念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并要求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二战”以后,现代艺术在美国获得了长足发展,相形之下,欧洲反而逊色不少。因此,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的展览和活动,希望重新拾起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被迫中断的现代艺术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趋势不可逆转,那就是现代主义分裂成了两个中心:欧洲和美国。
贝尔廷使用了德国的一个说法,把美国的现代主义称之为“二次现代主义”(或“二次现代性”)。当现代主义“旅行”到美国时,它的某些特征发生了变化,跟欧洲原初的现代主义有一些差异。“二战”以后,当欧洲国家的艺术家回过神来,沿着现代主义的方向追赶美国时,现代主义的性质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典型表现是现代主义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现代主义反对一切作为既成传统的“文化”。然而,当欧洲国家试图将一度中断的现代主义艺术事业延续下去时,人们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现代主义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传统,一种新的文化。鉴于现代主义在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人们也很难用“西方”一词来进行笼统的概括。
另一方面,在欧洲内部,现代主义出现以后的艺术传统也同样发生了分裂。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支配性的影响,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则是现实主义风格。由于评价标准完全不一样,因此无法就艺术的好坏优劣作出最终裁决。这种分裂尤以德国为甚。东西德统一以后,甚至原东德艺术家的作品能否跟原西德艺术家的作品一起展出,都成了问题。因为一方认为是纯正“艺术”的作品,另一方根本不承认是“艺术”。由此,现代主义本身的分化,以及它所造成的整个艺术领域的进一步分化,都给艺术史书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那种线性发展的艺术史逻辑显然已经无法处理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了。
另一种复杂的情况是,由西方的“艺术”概念向全世界扩展引发出来的。这种扩展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在非西方文化中的当代艺术和民族工艺品(ethnic artifacts)之间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民族工艺品不是在西方艺术的意义上制作出来的,也不被看作是艺术。与此相应,西方发展出两套博物馆机制,一套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另一套是民族学博物馆。这种体制也是现代性的遗产。原因在于,为了维护现代艺术的定义,就必须跟那些既不“现代”也不“艺术”的东西划清界限。在贝尔廷看来,现代艺术实际上在实行一种双重的排斥:一方面,它把 “艺术创作”直接等同于“现代艺术创作”,这样就把非西方的艺术家排除在外,甚至那些以现代派风格从事创作的非西方艺术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它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这样就把非西方的民族手工制品排除在艺术之外。(13)
为了弥合当代艺术和民族手工制品之间的鸿沟,出现了一种观念,即世界艺术,试图把全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囊括成一个整体。贝尔廷认为,这种关于世界艺术的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这种观念依然秉承着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信念,它在将全世界各民族的产品纳入“艺术”这个范畴的同时,实际上也用西方的观念对这些产品进行了改造。“世界艺术一直是指来自所有时期的艺术,也即人类的遗产。实际上,它使得来自任何地方的艺术都可以被接受,条件是将其排除在现代主流艺术之外,这是一种将艺术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相区别的陈旧论断。”(14)由于现代艺术只关心形式,因此,在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将各地的民族艺术吸纳进来是可能的,只是这样就会难以避免地改变这些作品的性质。
由于世界艺术这一概念会遇到上述困难,贝尔廷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概念,这就是全球艺术。他认为,“全球层面的艺术并不意味着可以从中识别出一种内在的审美特质,也不意味着对于被看作是艺术的东西有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它不代表一个新的语境,反倒是表明语境或焦点的丧失,它通过暗示在国家、文化或宗教各个层面都存在着地区主义和部落化的反向运动,从而表明自身也包含着矛盾。”(15)
在贝尔廷看来,当代艺术和全球艺术是一回事。他说,全球艺术“有如凤凰涅槃般于20世纪末从现代艺术的灰烬中生发出来并反对现代性所崇尚的进步和霸权理想”。(16)这就是说,作为全球艺术的当代艺术脱胎于现代艺术,但不再坚持现代主义的原则。由于“没有一种共同的艺术观念必然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社会”(17),因此,虽然当代艺术依然被称之为艺术,但“艺术”一词已不仅仅是现代主义普适性意义,而变成了一种地方性观念。可以说,当代艺术是西方的艺术概念扩展到非西方文化之后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它一方面不同于现代艺术,另一方面也不再是各地传统的民族艺术。
正因为当代艺术不同于现代艺术,所以它才有条件去解决西方艺术与非西方民族工艺品之间,或者说艺术史与民族学之间的二元对立问题。贝尔廷说,“我要冒险提出,在一个全球性的语境中,当代艺术可以侵入先前民族产品的领地”。不过他特意声明,他的意思不是“简单地承认民族产品是艺术,让它继续下去”。因为“一条鸿沟已经开启出来,一方面是已经穷尽和中断的本土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某些还需要界定、通常还没有进入博物馆的其他东西:当代艺术”。(18)
具体来说,由于当代艺术不是简单沿用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概念,而是根据本地的文化经验赋予艺术以新的内涵和功能,因此艺术与非艺术、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界限就不是那么壁垒分明。跟现代艺术不同,当代艺术已经不再局限于架上绘画,而是综合利用摄影、装置、行为、多媒体等表现方式。这使得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及跟观众之间的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在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博物馆、展览机制、拍卖行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博物馆在世界各地的大量兴建,会导致艺术概念及其评价标准不断变异,因为在贝尔廷看来,博物馆归根结底必须照顾本地观众的艺术观念和偏好。实际上,博物馆在当代艺术中的作用已经不同于现代主义时期。早先的艺术博物馆往往跟艺术史相表里,致力于展出经典作品,以便向观众提供有关艺术发展的清晰线索,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往往是现场制作的、其历史地位和意义完全无法预料的临时性作品。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新艺术通常会混淆主流艺术和通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因此它会抛弃旧的二元论,即把西方艺术和以本土传统为参照的民族志意义上的活动区分开来的二元论。”(19)
不过,由于当代艺术中包含着诸多的异质因素,我们无法把它纳入艺术史的框架。贝尔廷说,“艺术史,正如我在不同场合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局部游戏,只适用于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艺术。它被发明出来,是为了从形式的历史来研究艺术。实际上,当代艺术家故意离开了艺术史的主导叙事,他们用对后历史的拥护来拒绝艺术史的主张。”(20)由于当代艺术是一种全球现象,它既不遵循一种风格代替另一种风格的艺术史逻辑,也没有统一的发展方向。许多展览和事件往往是同时发生的,无法在它们之间建立线性联系。此外,我们也无法根据一个统一的语境来确定当代艺术作品的意义。因为它们可以在多个语境中获得多重意义。从全球范围看,当代艺术似乎正在变成一种地缘政治或地缘审美活动,而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活动。因此,它跟艺术史之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十分紧密,也很难用艺术史来描绘其整体面貌。“全球艺术往往逃避艺术史的论断,因为全球艺术不再遵从艺术史的主导叙事,也与现代性关于自己要成为或提供一个普遍性模式的声言相抵触。”(21)
这里似乎需要做一点辨析。贝尔廷认为,艺术史无法处理当代艺术,主要指的是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艺术史,即建立在“风格”和“线性时间”这两个原则之基础上的艺术史。用这样一个模式来囊括所有文化中的当代艺术实践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既不追求风格创新,也不构成一个连贯的时间序列。就此而言,艺术史的“终结”或“不可能性”主要是指宏大叙事的不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叙事也不可能。这里不妨套用利奥塔的说法,把艺术史模式从现代到当代的转变看作是从宏大叙事向各个层面的小叙事(地方叙事、国家叙事、个人叙事、私人叙事)的转变。实际上,正是这些小叙事之间的异质性才导致了整体性宏大叙事(现代主义)的崩溃。
三、时间与媒介的新变化
从字面上说,当代(contemporary)和现代(modern)意思差不多,都是指“现在”“当下”。哈贝马斯指出,“现代”这个词在最初使用的时候,是跟古代相对而言的,强调的是“现在”不同于“过去”。(22)然而,一旦在“现代”这种时间意识的基础上确立起一种审美的规范或“诫律”,“现代”也随之变成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了。同样,“当代”一词是由“共同”(com)和“时间”(tempus)两个词根构成的,指的是“同时代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一词的启用显然是为了跟“现代”相区别,因而,它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詹明信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对凡高和安迪·沃霍尔所画的鞋子作过对比。(23)他认为,凡高所画的鞋子是具体的,处在特定时间中;而沃霍尔的《钻石灰尘鞋》却没有来历,我们无法确定它在时间中的位置。他进一步把这种区别看作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未尝不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区别。
现代主义假定艺术有一个自律的发展过程,这种时间是独立于日常生活的,不受后者的干扰。但是,当现成品闯入艺术的领地以后,它也将日常生活中那种跟艺术完全异质的时间引入了艺术,并导致了艺术内部时间的解体。在对现成品的“挪用”中,远古的东西和晚近的东西处在同一个层面上,没有时间次序上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时间都已经平面化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时间已经终止,而是说,“挪用”这种创作行为抹去了艺术内部发展时间和日常时间之间的界线。当我们面对一件由现成品或现成图像构成的艺术作品时,我们需要面对两种时间:艺术自身发展的时间(风格的线性序列)和现成品所处的日常时间。按照现代主义的逻辑,首先必须假定每件艺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时间才具有意义;但时间对日常物品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是可以被随意替换的。
当代艺术中时间形态的新变化不仅体现在现成品上,同样体现在摄影、录像等新媒体当中。录像的播放和观赏都需要时间,这样就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和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观赏方式。不仅如此,由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摄影和录像设备来制造图像,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在贝尔廷看来,录像和新技术“在性质上”就是“全球的”,它们兴起的时间很晚,而且“没有艺术史的负担”,也“不依赖于西方的艺术史谱系”。(24)他甚至认为新媒体引发了一场“何为艺术”的观念革命:
艺术中的新媒体有着绘画和雕塑从未有过的全球性。它们提供了全球性的工具供全球艺术家掌握使用。媒介——略微改动下一个著名的定义——承载的是全球信息,因为它消除的不仅是中心和边缘的地理距离,而且还有文化距离。电影和电视以其平实的叙事使艺术对观者而言日益民主化。艺术与大众媒介分享工具或视觉语言,但又通过它的批判性信息与大众传播区别开来。“当代”已然成了电子化的表演。当艺术家们引入基于他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自身文化背景的陈述时,就向全球艺术又迈进了一步。新媒体在全球范围的一致性很快就被艺术中形式各异的信息抵消了,这些信息是从地域角度来再现全球性的整体的。这种使用也就解释了为何全球艺术在每个地方看上去都不尽相同。(25)
现代艺术追求的是风格和媒介上的纯粹和一致性。相反,当代艺术却体现出媒介、时间和语义上的复杂性。就新媒体而言,它们在当代艺术中的作用似乎是双重的。一方面,新媒体提供了可供全球共享的工具和图像语言,使艺术家从专门技术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当代艺术中,这些媒介表达的又是特殊的文化经验或个人陈述,从而体现出一种“地区化”或“本土化”倾向。实际上,贝尔廷之所以把波普艺术的全球胜利当作艺术全球化的另一个前提,也是因为波普艺术代表着媒介上的扩展。波普艺术广泛使用了大众媒介(报纸、杂志、广告、招贴)中的现成图像,跟大众媒介形成一种“游戏性竞争关系”。跟现代艺术对大众媒介的排斥不同,当代艺术可以从材料或技术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挪用,又加入了一些对媒介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媒介在当代艺术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艺术的意义问题。按照贝尔廷的分析框架,媒介上的开放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之一,如果当代艺术仅仅是使用全球共享的日常媒介(照片、录像、杂志插图、印刷品乃至现成物品)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丹托反复提到过的问题,即艺术作品和日常物品没有区别,艺术也不成其为艺术了。跟丹托的不同之处在于,贝尔廷是从图像与媒介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理解当代艺术的。按照贝尔廷的看法,当代艺术尽管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但它之所以仍然属于艺术,正是因为它具有跟大众媒介中的图像相对抗的性质。他明确说,造型艺术“以其独特的方式制作出来的图像,证明是跟我们每天消费的图像之流相对抗的”。由于“艺术的图像存在于可见性的边缘,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不可见和不可表现的深渊”,所以它们具有一种“语义上的复杂性”(26)。不过,不能把图像跟艺术作品混淆起来。贝尔廷说,艺术作品在被卖出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商品,具有了价格,可以打包发货,但图像却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灵中。“只有在观赏者那里已经唤起时,图像才存在:图像是我们在跟艺术相遇的时候重新认出的。”(27)
由此可见,在当代艺术中,媒介上的错杂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了对媒介本身进行反思,二是为了对抗日益泛滥的大众图像。当代艺术不排斥具象,但它也不是通过具象这种方式来再现“现实”,而是通过媒介之间的混合来激发人们熟悉的心灵图像。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家在使用图像的时候,往往会有意识地使媒介本身显现出来,或者作为一个因素在图像中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贝尔廷较偏爱的一个例子是日本观念摄影家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 1948-)。(28)杉本的代表作包括以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实景展览为题材的《实景馆》(Diorama,或译“透视画馆”,1976)系列,以伦敦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s)蜡像馆中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肖像》系列,以及《剧院》系列(1978)和《海景》系列(1980)等。(图2)《实景馆》和《肖像》系列拍摄的分别是动物标本和人物蜡像,即已经作为图像存在的对象。《剧院》系列的特点在于,照片的曝光时间是一部电影放映的时间,但获得的结果却是空空荡荡的电影院,没有观众,只留下屏幕上反射出来的一道亮光。《海景》系列拍的是很多不同地方的海景,但它们看起来都一样,完全失去了地点上的差别。
按照贝尔廷的分析,杉本的作品既涉及到媒介也涉及到时间问题。例如《剧院》系列拍摄的是电影院,这是另一种图像媒介——电影——被放映的地方,而且在建筑效果上跟戏剧的表演舞台很相似。在时间中流过的电影图像最后变成了照片中的空无。《海景》系列也同样如此,乍一看这是模仿以前的海景画;但我们从照片中能感觉到,在大自然那里,时间似乎是永恒和凝固的,这跟我们从地理位置和历史时间上对自然的切割、区分形成了鲜明对比。
杜莎夫人蜡像馆中有些蜡像是根据一些著名的古代绘画制作出来的。例如,亨利八世的蜡像是根据小荷尔拜因的肖像制作的。杉本博司拍摄这位国王的肖像,自然也是在参照荷尔拜因的绘画。因此,照片表面上是一张简单的亨利八世肖像,实际上却是这位皇帝以三种不同的媒介存在:绘画、蜡像、照片。时间的问题因此也被带了进来。(图3)正如贝尔廷所说,“当照片从一幅绘画的复制品上复制出一个人时,意味着是在回收图像。我们必须再一次问自己: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自己究竟处在什么时代?是在肖像被画成的时代?抑或是蜡像流行的时代?抑或是在摄影的时代?而摄影本身在这个数码时代已经变成了过去的媒介?”(29)杉本博司的作品既延续了“观念摄影”这种来自西方的当代艺术形式,又体现出了日本文化的内涵,他的作品因此可以同时从个人经历、民族身份和对西方艺术的反思等多个层面进行解读,而无法纳入某个单一的系统。实际上,整个当代艺术可能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艺术史的书写层面上,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获得一个普遍、共同的视角,来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艺术史框架,只能按照某个特定视角将艺术现象的某些方面联系起来,讲述一个局部性的、相对有限的故事。
注 释:
(1)See Anthur Danto, 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译本参见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Arthur Danto,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中译本参见丹托:《艺术的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3)(7) Ibid. S. 41.
(4)(8) Ibid., S. 43.
(5)(9) Ibid., S. 43.
(6)(10) Hans Belting, Art History after Modernism, p. 34.
(7)(11) Hans Belting, Das Ende der Kunstgeschichte, S. 46.
(8)(12) Hans Belting,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Museum in the Global Age”, in: http://www.globalartmuseum.de/site/act_lecture1 (2011-11-12); 中译文参见贝尔廷:《全球时代的当代艺术与博物馆》,周飞强、白燕清译,载《美术馆》2008年第1期,以及贝尔廷:《全球化时代的当代艺术及艺术博物馆》,载陈漫兮编:《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2009中国当代艺术理论批评研讨会论文文集》,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
(9)(13) See Hans Belting, “Contemporary Art as Global Art: A Critical Estimate”, in: The Global Art World: Audiences, Markets, and Museum, Hans Belting & Andrea Buddensieg (eds.), Ostfildern: Hatje Cantz, 2009, p.55.中译文参见贝尔廷:《作为全球艺术的当代艺术:批判性评估》,杨荣芳译,周彦译校,“中国当代艺术国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70e2e90100dedq.html (2011年11月8日访问)
(10)(14) Hans Belting, “Contemporary Art as Global Art: A Critical Estimate”, in: The Global Art World, p.41.
(11)(15) Ibid., p. 40.
(12)(16) Ibid., p.39.
(13)(17) Hans Belting,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Museum in the Global Age”.
(14)(18) Ibid.
(15)(19) Hans Belting, “Contemporary Art as Global Art: A Critical Estimate”, in: The Global Art World, p.40.
(16)(20) Ibid., p.45.
(17)(21) Ibid., p.69.
(18)(22) See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ited by Hal Fost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3-15.
(19)(23)参见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载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0-515页。
(20)(24)See Hans Belting,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Museum in the Global Age”.
(21)(25)Hans Belting, “Contemporary Art as Global Art: A Critical Estimate”, in: The Global Art World, p.59.
(22)(26)Hans Belring,Sisyphos oder Prometheus?“,in:Szenarien der Moderne: Kunst und ihre offenen Grenzen, Ausgew?hlt und eingeleitet von Peter Weibel, Hamburg: Philo & Philo Fine Arts, 2005, SS. 298-9.
(23)(27) Ibid., S.300.
(24)(28)关于贝尔廷对杉本博司作品的详细分析,参见Hans Belting, Looking through Duchamp’s Door: Art and Perspective in the Work of Duchamp, Sugimoto and Jeff Wall, Kln: Walther Konig, 2010.
邹建林,男,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