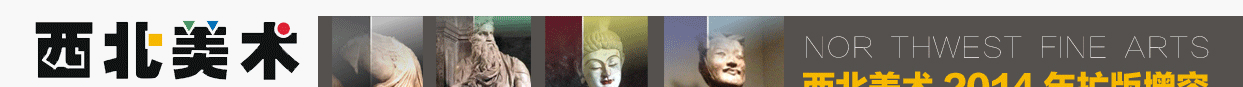摘要:本文阐述了美学的自我构建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旨在通过对惠能的研究来探讨唐代精神。笔者提出,惠能将感官与悟道相联系的方法有助于对艺术史的研究和对中国山水画文化价值的欣赏,认为牧溪画作中的“空寂”与“无形”并非模糊不清,而能与构成有情个体自我真性的感观存在领域共鸣。
关键词:美学;惠能;《坛经》;唐代精神;感性存在
当代中国画家通过弘扬本土文化传统在全球画坛独树一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美学家正试图解释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帮助中国画家从中获益。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唐代的思想与美学观念能否引导当代中国画家表达创作思想并使其在全球引起共鸣?唐代精神能否为当代艺术史家提供新的思维方法来描述传统中国山水画的永恒价值?
就唐代历史文化之于中国美学而言,影响深远的一位禅宗六祖惠能的著作可谓良好的研究开端。此处要验证的假说是:对于画家,评论家和有兴趣于自我与形象显现及“天人合一”的理论家来说,惠能的《坛经》依旧是宝贵的思想资源。作为一个外国的画家和美学研究工作者,笔者明显地感觉到欧美对于美学自我构建和写实风格的描述明显言之有失。笔者在此就惠能的文本及其对当今个体感性存在的认识提出粗浅看法。悟道不仅指心灵的宁静和虚空,还指个体自性及其与万物的不可分割。通过研究《坛经》,我们可以创建一种特有的感性存在领域的语言,使其成为画家更能明确表达中国绘画作品真谛的,更有研究价值的艺术史的共有主题。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亚洲和中国的绘画作品为何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密接触,而这种接触在欧美自然与艺术哲学中通常是被忽视的。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美学自我构建和道德发展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了伦理学传统治学方法中“道心”与“人心”的冲突,即天理与“感性血肉”的“纠缠”。美学家李泽厚认为这一冲突始现于明朝晚期。他更明确地指出,伦理学与形象显现人类(“心”与“身”)的冲突是新儒家美学的特点。他还发现了王阳明试图将道德法则与形象显现生活互相结合时产生的矛盾。李泽厚对王阳明的批判向每一个试图从惠能的禅宗悟道精神那里获得灵感的现代人提出了挑战。挑战之所以产生,在于《坛经》表达了佛教的一元性原则:智慧与形象显现密不可分,合为一体。本文旨在通过对惠能的研究来探讨与支持唐代精神,因此笔者需要解释《坛经》在李泽厚对王阳明的批判中如何才能不受冲击。作为对李泽厚文章的回应,笔者的结论是心物一体(梵我一如,一元论)的哲学思想未必会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与作为历史运动的新儒学中道德与审美意识的解体。笔者将要指出的是,理查德·罗蒂关于强力诗人审美生活的描述对当今以显现经验的审美生活为基础构建道德法则的任何尝试都提出了相似的挑战。
《坛经》中“见性成佛”的思想为今天的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存在一种能够成为同情原则与美学自建基础的形象显现。笔者认为惠能启示我们对形象显现的感性存在采用第二种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摆脱伦理学与人以客观体验方式接触自然的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道”与“心”的冲突)。如果我们最终发现惠能成功地将形象显现的感性存在与同情众生的道德框架合为一体,我们就可以探究王阳明是否也提出了相似的形象显现与道德价值统一的,不受李泽厚批判的哲学观点。然而,出于本文的目的,笔者将把自己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惠能及唐代精神给我们的启发。
惠能的《坛经》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明心与见性的篇章,即“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然而要想直白“真如”或“见性”是相当困难的,笔者认为此词被用来表达由不同感官所呈现的只对个体展示的感性存在。比如,每个人的眼睛都会提供一个唯一的、稳定的感官领域。这一感官领域证明其在感知有形物体和从事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具有一个肉体的存在。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试图表明“真如”一词在欧美比较美学和宗教哲学的文本中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重要的工作尚需更具水平的专家学者来完成。同时,欧美读者需要并期待中国同仁对“真如”一词做出全新的解释。告知这一点非常重要。惠能的《坛经》成功地表达了个体感性存在的观念,而这正是同情众生观念的存在基础。这对于抽象的,非形象显现的和非存在主义的,以欧洲哲学中康德的崇高论为特色的道德和审美快感研究方法来说是一个颇受欢迎的选择。
本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提出惠能把感官与悟道相联系的方法有助于对艺术史的研究和对中国山水画文化价值的欣赏。
建议读者进一步加强对高居翰有关牧溪传统中国山水画的阐释。牧溪作为南宋禅宗画家,寻求萧散虚和,不拘法度。其画作中的空寂与无形并非模糊与不清,而是与构成有情个体自我真性的感观存在领域形成共鸣。
一、传统与现代形象显现:伦理学与血肉自身的冲突
在《华夏美学》一书中,李泽厚把惠能看作在生活中悟道的禅宗思想的核心人物。为了支持惠能关于悟道的阐述,笔者愿就李泽厚关于禅宗美学的评论与读者展开对话。李泽厚认为在王阳明的新儒家美学中,存在着道德法则和人类形象显现之间的冲突。王阳明的哲学中包含着禅宗美学的一些范畴,比如顿悟和有关自性与肉身生命的一元性思想。因为禅宗美学的思想既属于王阳明的门径又属于惠能的方法,于是要想肯定惠能《坛经》中体现的唐代精神,就必须首先去除李泽厚对王阳明的“批判”。李的批判始于两个前提:王阳明认可“天理即人欲”把道德与肉身生命合二为一及形象显现生命由人对客观事物的体验构成。基于这两个前提,李泽厚得出结论:“人类个体的肉身生命是一个物质的形象显现,它不能为道德准则所需的绝对价值提供不变的基础。”笔者首先重温这两个前提,然后仔细估量李泽厚对王阳明一元论的批判。通过探讨李泽厚的批判的细节,我们将会明了支持惠能《坛经》和唐代精神的具体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声称在王阳明理论中所发现的冲突——假定存在于传统道德与形象显现的血肉个体之间的冲突——正与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主义哲学遥相呼应。罗蒂认为形象显现诗人的审美生活无法与哲学家的道德生活自然适应。他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把美学自建生活和具有道德与正义法则的形象显现体验结合在一起。既然这种对立不可避免并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罗蒂因此倾向于以创造性诗人的审美生活方式建立一种共同体。他认为那种可以在每个人都假定会有的无形内在本质基础上建立道德共同体的传统观念并不令人满意。最后,罗蒂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生活是由自由与自主的自性组成,自性全由经验组成,而这些经验并不构成可由他人评估的、稳定的统一体或终极价值基础。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罗蒂的哲学对于固有的“自性”不着笔墨,而这个“自性”正是个体自行判断经验真实性并将其与另一经验真实性进行比较的依据。自我创造变成了一个只由经验数量和个人品味判断的任意过程。罗蒂对于审美生活的描述与李泽厚归于王阳明的感性存在生活的说法相差无几。罗蒂关于个人审美生活中道德准则缺失的后现代论述在李泽厚对王阳明的解读中同样可以听到回响。根据李泽厚对王阳明的解读,道心与只是物理性质和没有绝对价值的事物的人心密不可分。据此李泽厚认为,强调与肉体不可分割的哲学不能提供道德引导和对人欲的约束。
因此,我们探讨惠能的目的就在于希望避免李泽厚在现代生活中发现的伦理与形象显现的冲突,以及困扰着罗蒂文化哲学的诗歌与哲学对抗。
慧能认为,自性即佛。自性不是诸法的自性,而是人的自性。在大千世界中,唯独人是有自性的,也就是有佛性的,概无例外。要肯定惠能的《坛经》,就有必要说明自性如何指的是个体感性存在中的可观察元素而非个体对其形成喜好的人类的经验对象。李泽厚认为王阳明的哲学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滑离:即因滑离了关于自我与体现一元论的前提,而导致认为形象显现是物质的从而不能为人类道德共同体提供一个不变的价值基础。为了避免这一滑离,我们需要仔细探究李泽厚对王阳明和佛教梵我一如的批判性评价。在此之后,我们方可探讨惠能的《坛经》以寻找第二种非常不同的,不由自然与物质存在决定的形象显现的迹象。
二、李泽厚论王阳明:物质形象显现的问题
李泽厚认为王阳明的理论导致新儒学强调自我修养与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走向崩毁。让我们就此展开评估,评估得越透彻,就越有机会发现该如何反驳认为惠能的理论包含同样矛盾的指责。笔者在此重申,李在王的一元论哲学中所发现的问题是:包含一个超越不断变化的自然界的先验原则的“道心”依附于或不可分割于从属人体与物理性质的“人心”。李认为感性主导代替了理性主导;道德良知混同了感性元素。按照李的观点,其结果就是人类的思想变得更依赖经验而非理性,而新儒学思想则变得益发具有物质主义性质。李泽厚认为,王阳明的天理与人心不可分割的一元论主张一旦成立,上述这些问题都会随之产生。
要注意的是李泽厚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背景前提之上,即形象显现或他所称的“情境”必然是世俗的,并总是由对物质形象显现的认识而决定。简言之,李泽厚的论证似乎始于这样的假设,即形象显现或个体肉身生命必然是种物质的、生物的或就第三方所知需靠经验来理解的状态。因此,按照李泽厚的思维方式,王阳明的哲学把明心见性和认识物质体现看作不可分割。李本人并未停下来思考是否存在另外一种与生俱来、独一无二、任何人或第三方都不能客观体验的个体形象显现,而是继续如下解释王阳明心理合一的一元论哲学,即不再需要理性来束缚人心,于是束缚人生追求所爱物质的精神源泉不复存在。对李泽厚而言,现代血肉个体观念的出现使得哲学走向强调个体创造性和性灵物质性的道路。由此推断,自性对于有形物体验的依恋使李泽厚断定个体感性存在无法展示使个体有资格成为道德共同体一员的任何绝对价值。从李泽厚的假设来看,形象显现与血肉生命基本上就是追求物质的生命,理性的人很可能被诱使断定道德法则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破坏性冲突根本不可避免。
那么是否有证据表明李泽厚曾以可以客观认识的物质形象显现来解释人类个体感性存在呢?李确实说过:对人类感性存在的提问就是对人类实践根本的提问,就是对“本体”的提问。他进一步指出,对事物根本的研究与考查离不开先行的社会实践。正是通过使用工具人类才构建了认知、道德与审美的社会存在。李还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血肉个体自性重要性与奇特性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考虑到感性存在决定于已知社会状况的假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认为“本体”或人类实践的根本就是由第三方凭借经验了解的客观状态或过程。因此,根据李的描述,血肉个体的感性存在是产生心理建构和精神“本体”的物质条件。简言之,李看来确实支持个体感性生活(或血肉个体意识)决定并产生于外部条件和物质需求这一背景前提。
然而假设感性显现原本就是物质的、客观的,由第三方体验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认为对他人而言非物质的任何形象显现都是非客观的,因而只是想象出的抽象概念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支持惠能与唐代精神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李泽厚关于个体形象显现的背景前提提出质疑。在此所讨论的问题是李泽厚关于个人感性存在必然是凭经验了解的客观存在这一显而易见的前提。正是这一前提使李泽厚得出自性与自然形象显现的不可分离性与道德原则的构建无法共存的结论。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欧洲哲学传统趋于认同李泽厚的前提,以及其关于自我形象显现总是作为经验对象而被体认的这一推论。康德认为,没有哪一种外在的经验对象能够具有稳定不变的内在价值而作为道德法则被所有时代的所有群体所接受。因此,从李泽厚对于感性存在所给出的客观的。经验主义的定义来看,追求客观对象的形象显现生活似乎确实不可能包含道德法则的内容。于是,我们如何定义“形象显现”就十分地重要了。对于定义的不同选择将决定哲学家们是否能够在个人感性存在中找出道德法则。
对于个人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与生俱来的,他人无法获取的而仍然具有感性的形象显现是否存在第二种解释呢?如果存在第二种解释,那么形象显现生活就实质上不是对有条件的,其价值不断变化的客观对象的依恋了。凭借第二种可以选择的解释,李泽厚关于个体感性存在就是物质存在的推论就可以终止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李泽厚对于中国哲学中万物一体思想的信奉可能同时导致他提出一种虽无客观存在却又真实不虚的,并非想象的个人感性存在。李明确地提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体感性存在。似乎任何一种完全彻底的,独一无二的感性存在都是非客观的和非己莫属的,虽然李并没有明确强调这一含义。无论李泽厚是否有意为之,其就形象显现的感性存在所提出的,具有前卫和非客观内在性的第二种解释,正是笔者希望通过研读惠能的思想来获取的。
笔者想问的问题是,是否每个人都有能力注意到那些并非身外之物或者实践活动的形象显现元素。如果要支持惠能的禅宗美学而反对李泽厚对王阳明的批判,我们就需要对个人的个体感性存在中的非物质元素进行描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指望惠能使用“自性”一词来代表不能作为人所欲求的实物来体验的某种感官领域。
通过研读唐代的《坛经》,我们希望找出某种既见于个人又见于众生的感性形象显现中的非物质元素的命名方式。对于与生俱来的,非客观的,不作为客体被自己或他人感知的感性存在思想的发展来说,《坛经》确似大有作为。
三、惠能与智慧:感官,众生与同情的启迪
《坛经》中有数章促使我们关注无法以偶然的客观对象或事物的形式来客观体验的自性形象显现的实例。比如,惠能在谈及顿悟见性和获得智慧时多次提到了脱离具体感知物体的感官存在,瞬间若流水花开、鸟飞叶落,达到清静永恒,超越一切因果。说到见性时,惠能强调了“真如”一词。所谓“空相”指的是排除干扰的手段。只有排除干扰,人体才能明心见性。正是“真如本性”一词有可能帮助我们就与生俱来的,非客观和非物质的形象显现的感性存在提出第二种后现代的解释。只有认识到自性与真如不可分离(而与对客观事物的体验又可以分离),我们才可能有机会证明惠能关于自性和肉身合二为一的学说也许能为我们提供道德法则与社会合作。
“一切般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人。”最重要的是,惠能的《坛经》告诉我们要想洞见真如就要净本心,出六识,除六尘。思想可由特定感官产生而不被污染,感官的认识可不由经验或感知感官所偶然展示的特定感知对象而生成。视觉现象不同于眼睛,而眼睛与视觉现象又不同于个体可以区别现象的真如的真实范例。通过去除对特定事物的感性思考来获得心灵的净化是如来或者一个自见真性者的任务。因此,即使在伴随着智慧生成的宁静之中,也仍有指向感官之一的思维存在:惠能明确指出转迷开悟的大事,不能用空心静坐这些小道来获得。开悟获智来自于树立一种自真如的真实范例而生的观念。正是因为由感官展示的真如范例产生出这一观念,人才能够(像如来那样)认识到人的自性始终都会显现。只有通过如来净化感官,感官才可以在至少是某些场合被当作真如的持有者来观察,而不总是被当作可以明确感知的事物或有关物质利益的事件来观察。视觉器官可以看到飞鸟的外形,但是如来却需要“净化”所见外形才能使人们看到真如,而不是变化中的物体的外形(飞鸟)。
真如或本性与用眼观察到的视觉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对我们解释与评价惠能的《坛经》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惠能鼓励我们每个人对形象显现提出第二种解释:人眼作为感官展示了一个可观察而又非客观的感性存在。当这一存在作为真如持有者被观察时,人的眼睛会提供一个独有的、外在第三方无法体验或核实的感性存在实例。而且,真如是在一个或更多不同的感官中展现的;比如,它通过人的眼睛或在人的眼睛中展现出来。但是以神经科学家从外部观察事物时所用的眼睛来识别真如是不正确的。
就眼见而言,真如或自性是一个独特的感性存在领域,它在个体对视觉现象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同时存在。惠能的《坛经》认为真如是自我真性的真实范例(于观者自身显而易见)。笔者建议如下解读其文本:人们在观察事物时只要不执著于具体的形象或事物,人的视觉器官就可以自见真性。一切凭视觉感受的事物都会在人眼所及的范围之内展现。属于有情个体自性的可视领域与通过个体感性存在观察到的,展现事物原貌的领域并无差别。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如来能够看到一个具有感性存在质理的可视领域。虽然可以看作独立领域,但当意识插入对特定形式、形态或结构的感知的思考时,这个领域却不是视而污见就是视而不见。
《坛经》中说,人人有佛心,万物皆平。人人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笔者提议采取如下解读方式:人的眼睛展现了一个真如的真实范例,这一范例可以被看作本性视觉现象通过个体而展示的可视领域。虽是非客观的,而且没有客观的,可体验的存在,但对于观察个体感性存在和个体在本质上所见的事物原貌来说,真如依旧是根本的可视元素。虽然可视领域的质理以眼中灵性而展现,对于明心和见性来说,这一质理却是基本原则。自性的观念产生了感性存在思想,这一思想是个体的,非客观的和形象显现的,因为个体所见的的真如范例属于个体视觉器官和个体形象显现。通过对可视领域(真如范例)的思考,明心最终会使如来(如实感觉自我真性者)为有情众生设计出更大的道德共同体。如此,同情的原则产生于自身真性范例:有情众生皆应获得帮助与扶持。如果我们如此尝试,把视觉真如看成一个可视领域,那么(建立在自我与个体感性存在的统一基础之上的)禅宗一元论思想就有可能与同情这一道德法则相互兼容。与传统道德的不同之处在于:惠能所描述的同情原则的内容(真如,可视领域)既不是一个可以理性理解的经验对象,也不是纯粹理性。
惠能的《坛经》也许能为非客观的感性存在解释提供所需的帮助。感官是感性存在的前客观媒介,它能给个体提供直接的,“原始的”梵我一如的证据。其次,惠能明确指出,以六尘来认识世界是一种玷污;这与感官在悟道过程中存在启发作用完全不同。以六尘来认识世界会妨碍智慧的获得;但只要不离自性,借助于感官反而会促进智慧的产生。惠能没有表达通过体察别的求悟者来获取客观知识的第三方的观点,只是把自身的感悟告之于人,“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视自性,一悟即佛地。”其文本是从关注自身感官(比如眼睛)的人的角度来写的。人能够注意到与自身感官相联系的自性;而无法直接观察别人感官所看到的真如。
能为有情众生提供道德法则内容的第二种形象显现解释已经出现,关怀有情个体存在的道德法则已经产生,它似乎能避免李泽厚认为王阳明哲学中所存在的矛盾。李泽厚的批判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真如是非客观的,与生俱来的,无法理解的,以及作为物质无法体验的一个可观察形象显现的基础。自身佛性与形象显现合二为一的思想不会导致物质主义哲学和无法为道德法则提供绝对价值内容的物理对象。《坛经》使我们从含有现代思想的,认为身体束缚和限制欧美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假设中脱离出来。进一步来说,如果明朝确曾出现过新儒家美学崩毁的迹象,那么从历史来看,这一衰落并不源于自性与悟道统一于形象显现的禅宗思想。
《坛经》可给当代中国画家带来灵感,使他们创作出能够唤醒人们去认识他们在观察事物时会忽略的可视领域的作品。我的部分假设是:惠能的《坛经》为个体感性存在指出了一个特定的含义,而这一特定含义能为真正表现天人合一的绘画作品提供可见内容。
四、可视领域和有情众生:中国山水画的全新解读
这一切如何为绘画史和中国山水画的解读提供可用语言?这一语言怎样帮助我们对今天仍旧能够提供道德与哲学指导的中国山水画传统进行评估?我们的结论是有必要对当代艺术史的术语进行修正以使其适应对亚洲和中国绘画作品内涵的表述。惠能关于“真如”属于感性存在和自我真性领域这一思想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个体所看到的可视领域就可以成为画家绘画作品所展现的主题。认为过去的中国画家已经注意到眼中所见的“真如”这一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可能已经尝试过表现山水画中的感性存在,来传达自然界中的生气与人的感性存在密不可分这一理念。这种绘画理念在欧美绘画中似乎现在和过去都不曾有过。
通过赏析牧溪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惠能的语言会如何丰富我们对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理解。高居翰将牧溪归类为文人画家:他认为始于唐朝的泼墨写意画到了牧溪的时代已经完全成熟。因为牧溪曾住持佛寺,高居翰对禅修与文人画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示赞同。高注意到二者的密切关系:禅修的过程和文人画的创作过程都提供了直接悟道而无需对物理对象去做含有理性认知的冥想。因为见性是刹那间的,所以高居翰注意到只有凭借个人才能获得不同于对事物进行一般的理性体验而获得的认识。因此高居翰总结出佛教禅宗不为人指引“著相”的悟道之路。他还总结出禅画日渐衰落,已为现今截然不同的、追求形似的绘画风格所取代。对于牧溪的《渔村夕照图》高居翰是如何评价的呢?他认为牧溪的画作展现了“简略的笔调”“重复的形式”“疏落的暗影”和“大片的余白”及其他“依稀、间或空濛”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高居翰没有以空濛或飘渺为题来探究自然活力的真实再现,而是回到欧美追求形似的美学标准并以之对牧溪画作的价值进行评估。他认为自北宋以来对外部世界进行现实主义描绘的山水画传统已最终成熟于类似《渔村夕照图》的文人画风。他写到此幅画作有一种“简化了的,印象主义的,而又咄咄逼人的意象”。
通过对比,借助惠能,我们就可以发现属于完全独有的个体感性存在的,对于非客观和非客观感性存在进行再现的牧溪绘画作品的重大意义。要看到牧溪绘画作品的意义,我们不必退回到现实主义标准。可以把牧溪画作的空濛性质归结为技艺熟练的手段:作为一座禅院的创建者,牧溪以绘画的方式来展示直了成佛怎样成为标志自性与实相的“真如”的独有范例。再如,高居翰认为玉涧的《庐山图》一画展现了“无限与神秘的空间”。凭借着惠能的感性存在语言,我们可以说《庐山》一画形象再现了一个瞬间。在那一个瞬间,画家认识到自然现象也就是并不神秘的真如,也就是自见真性的媒介。
唐代的精神和惠能的《坛经》也许可以帮助学者们对感性存在和传统中国绘画中的文化价值提出全新的解释。本文写作的部分动机既来自对存在于罗蒂美学自建的后现代理论中的主观臆断的不满,也来自对欧美绘画史关于中国传统山水画含义与价值语焉不详的思考。笔者认为,惠能的《坛经》对于时显狭隘、不够完善的欧美美学与艺术史研究方法来说,可以成为一种颇受欢迎的补充。惠能的《坛经》表明禅宗的精神能够为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的中国美学做出重大贡献。李泽厚所预设的现实社会与道德法则的矛盾在惠能那里并不适用。此外,如果笔者对于惠能思想的提议尚能服人,那么禅宗智慧就不是芸芸众生看破红尘,悟得真性的阴郁思考,而是适用于美学,可以照亮感性存在和万物本真及众生价值的除暗明灯。自唐朝以来的惠能思想中表现出的禅宗美学理念可以激发当代中国画家和美学家产生新的思想,为世界美术和美术评论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惠能.坛经(英文版)[M],译者:A.F.Price and Wong Mou-lam(Boston: Shambhala, 1990) 195页。
[2]李泽厚.华夏美学(英文版)[M],译者:Maija Bell Same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0), 185.
[3]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英文版)26,40页。
[4]李泽厚,《华夏美学》(英文版),198页。
[5]李泽厚,Jane Cauvel,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View(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p.40。
[6]此处“感性存在”定义由卡尔·马克思1844年在其著作中提出。《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文版)译者:Martin Milligan (Buffalo: Prometheus Book,1988),p.154。
[7]李泽厚,Jane Cauvel,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View(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41页。
[8]出处同前,42页。
[9]惠能,《坛经》(英文版),85页。
[10]出处同前,97页。
[11]出处同前,97页。
[12]高居翰,Chinese Paintings, XI-XIV Centurie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pp.19-20。
[13]出处同前,20页。
[14]出处同前,37页。
(潘寅 杨文 译)
大卫·布鲁贝克(David Brubaker)(美国):男,美国纽黑文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