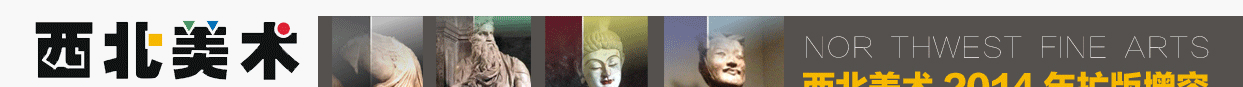摘要:中国艺术史的一个永恒真理是,当母题保持不变或被重新复兴时,风格依旧变迁,只有在考古学家和风格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方有可能为风格特性分析提供坚实可靠的知识背景。科学的风格分析理论是伴随西方艺术史家研究领域的拓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描述中国艺术史,需要一种能服务于其他诸如文学、思想等文化活动的结构。本文运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文献学和艺术考古学出发,将中西方艺术理论家的学术观点及中国商周青铜器实物资料结合,以此作为研究中国青铜时代艺术精神的方法与途径。
关键词:青铜器;艺术风格;考古;商代;西周;东周
一
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作为研究古代历史的两种途径,在中国有着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中国历代学者素有好古的热情,他们对过往的追溯累积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发掘和收集人工制品的考古学研究,大约始于一千年前的宋代。当时的金石学家欧阳修(1007—1072)在《集古录》跋尾云:
嘉祐中(1056—1063),刘敞为永安守。长安为秦、汉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没于荒基败冢,往往为耕夫牧竖得之,遂得传于人间。刘氏喜藏古器,由此所获颇多。(1)
刘敞收藏了11件青铜礼器,他让画工摹写其文,图绘其象,然后刻于石上,名曰《先秦古器记》。在其序言中,刘敞论及了古铜器研究之方法:
曰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2)
欧阳修编撰于1061年的《集古录》一书,是中国最早的金石学著录之一。1092年,另一位金石学家吕大临编撰了《考古图》,该书著录了自御府之外37家所藏的211件古铜器和13件玉器。吕氏让画工摹绘其形,并将古器出土地点、收藏之家及大小尺寸一一标注。其后,又出王黻《宣和博古图》一书,书中著录了宋徽宗宣和殿所藏古器839件,分为20小类,每类皆配之图像和释文,其器之大小尺寸、容量轻重亦有标注。
尽管这些著录在性质上属于古物研究而非考古学分析,但一些秉持中国理性怀疑精神的学者,却能用一种近乎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探究相关的问题。譬如,北宋学者沈括(1031—1095)通过对出土古物的切身观察,对当时儒家《三礼图》唯心捏造、篡改古彝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披露。(3)
然而,传统的中国古物研究,亦即所谓的金石学,主要着眼于对铭刻的著录和分析,以此来作为“补经证史”和“效书”的工具。基于田野发掘的近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只是到了20世纪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1928—1937年之间,围绕中国古史的考古学研究,引发了一场重要的学术大讨论。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次对安阳殷墟进行了科学的发掘。二战爆发后,殷墟考古发掘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田野发掘工作才得以恢复并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的规模。
1949年,中国青铜器、神话及古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郭沫若(1892—1978)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任文化部部长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职。经郭沫若提议,并经周恩来总理批示,文化部增设了专门保护古代文物古迹的行政管理机构——国家文物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挂牌成立。自此以后,所有的考古发掘活动便在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的双重督管下进行。考古研究所承担重要的田野发掘工作,并负责出版考古发掘报告。郑振铎先生担任文物局首任局长及考古研究所所长,后来又升任文化部副部长。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版本学家,郑振铎为搜集、整理民族图书和文物殚精竭虑。遗憾的是,1958年的一次飞机失事终止了他所钟爱的事业。(4)郑氏逝世之后,王冶秋同志继任文物局局长,在其卓越的领导下,一度陷于停滞的文物清理、保护和发掘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文物局也成为国务院领导下不可或缺的一个行政机构。
在学者型政治家当中,郭沫若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代表。(5)1913—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学习西医期间,系统研习了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7年,因政治原因,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一直到1937年。流亡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学和古代社会的研究之中,对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作力尤甚。1929年,郭沫若翻译了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美术考古一世纪》(郭的译著名称是《美术考古一世纪》,尽管应该是“艺术”)一书,并从中领悟了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6)
1930年至1932年,郭沫若先后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两部重要的著作。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郭氏确立了中国青铜器独特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他立足于周代青铜器铭文,通过题铭识读、历史及风格的综合分析,从中筛选出251件(323件为更大范围的划定)有确定年代和出土地点的器物作为标准器:“对于青铜器年代的推定,先据铭文中透露年代的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之有人名事迹可联系者,然后更就文字的体例、文辞的格调,及器物的花纹、形式以参验之。”(7)
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文化部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郭沫若和郑振铎对当时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做了针对性的发言。郭沫若在开场白中如此赞颂中国古物学的研究传统:
《考古图》和《博古图》所处理的范围虽然主要只限于青铜器,但它们对铜器的花纹、形式、度量、时代、铭文的考释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有时候联系到历史地理,有时候联系到工艺技巧,公平地说,是具备了一个相当严密的学术传统的……北宋以后,关于这门学问的研究在我们却不幸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衰落下去了。一直到近代主要由于西方的考古学的输入,对于这门学问的研究热情又才逐渐恢复了转来。(8)
尽管郭沫若接着列数了当时考古工作的一些成就,表扬了北京大学为国家培养了341名田野考古人才,并且肯定了他的同事们为考古工作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但在最后的发言中却不无严肃地告诫大家:
中国的考古事业具有世界性的深刻意义。人类史和世界史还有很大一片空白,急切需要由地下埋藏极其丰富的中国来加以补填。
郑振铎的发言,对今后考古工作提了五项建议:
1.考古学是研究人类物质文化的科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
2.加强学术研究工作,要为12年内赶上世界考古学水平的目标而努力。
3.做好配合国家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的文物清理工作,特别是那些应该走在工程队之前的发掘工作,决不能等到工程开始后才实施文物保护工作。
4.密切联系群众,运用群众的力量,做好考古工作。
5.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培养少数民族的考古工作干部。(9)
郑的五项建议,确立了此后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规范。早在1950年年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各个省、市为了贯彻执行法规,都前后陆续成立了诸如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化局、文物局或博物馆等各级文物管理机构。
1977年秋,中国古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受邀出席了此次大会,这是我阔别祖国30年后的首次回访。会议期间,承一位中国好友相告,得知当时除北京大学设有专门的考古学系外,另有八所高校在历史系开设了考古专业课程。此外,还有很多省级和地方性的博物馆也训练、培养相关人员。如南京博物院内设考古研究所和书画、工艺研究所,每所约有30位科研人员。博物院组成专家讲解团,利用幻灯和其他培训材料到乡村和农场宣传、普及各种文物保护知识。农民、工人在劳动生产中一旦发现地下文物,便会立即上报当地的文化局或博物馆,当地的文物管理单位再将这些信息上报到国家文物管理部门。得益于老百姓对考古实物认识水平的提高,各地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也得到有效的加强。
二
19、20世纪之交,考古学逐渐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1908年,备受郭沫若推崇的考古学奠基之作《美术考古一世纪》最终问世,作者米海里司(Aldolf Michaelis ,1835—1910)在书的末章《发现和科学》中,论及了风格分析方法在艺术考古研究中的独特作用:
较诸于以往依赖于某一假定可靠的(文献)框架——此框架虽有文字依据,实际却颇不充分且价值甚微,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充溢形式与色彩的结构……艺术品有其自己的语言,艺术史学家的职责乃对之加以理解和诠释。(10)
科学的风格分析理论是伴随着西方艺术史家研究领域的拓展——从起初专注于西方古典时期扩展到非古典(罗马晚期、巴洛克)风格、手工艺品(地毯、编织品)和非西方(埃及、东方)艺术形式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如此巧合绝非偶然。风格史学家分析一件艺术品的方法和技巧,向来不考虑国别、种族和时代。凭借宣称其在客观现实范围内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主张,科学的风格分析把一件艺术品的形式特性看成是一般问题的特别解决方案。
为了探寻艺术的起源,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1803—1879)试图通过研究、梳理各种个体作品所呈现的资料情况来推断艺术的普遍性原理。(11)森佩尔相信原始的装饰艺术导源于编织技术,并由此推断艺术的起源乃是材料、实用目的或功能、工具以及技术相互作用的产物。他对一件艺术品风格问题的阐释,很大程度上依据于材料的机制特征以及制作的技术问题。
出于对森佩尔“有害的唯物论哲学”的不满,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在其《风格问题》(柏林,1983)一书中提出了“艺术意志”(artistic volition)这一重要的学术术语,认为艺术家的心智活动才是艺术的根本源头。(12)李格尔的“艺术意志”理论有助于说服同时代的人们能够以一种客观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对待不同种类、不同时期的艺术品。作为维也纳工艺美术博物馆纺织部主管,李格尔还撰写了《古代东方的地毯》(Atorientalische Teppiche, 莱比锡Leipzig,1891)一书。李格尔认为,艺术史是一部从触觉的知觉方式向视觉的知觉方式不断进化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艺术总是对前一阶段更高形式的发展,这种进化和发展与知觉的客体向知觉的主体在艺术思维活动中的进步是一致的。
按照佛莱克林(Paul Frankl,1878—1962)的说法,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最先“摆脱理念或形式的局限,探析艺术作品本身……其所指涉的概念不是美学而是艺术学意义上的”。(13)布克哈特继任者康拉德·费德勒(Konrad fielder)坚持艺术就是形式的观点,他将形式进一步界定为“艺术的塑形”。费德勒之后,雕塑家阿道夫·希尔德布兰德(Adolf von Hilderbrand,1847—1921)继续探究雕塑和建筑“看”的心理过程,宣称“艺术是用‘眼睛’来塑造、表现形态”。佛莱克林总结道:
康拉德·费德勒仅仅指出尚待探究的一些东西,而希尔德布兰德也只是在片面评估风格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少许新概念而已,只有沃尔夫林提出了大量富有创新的洞见,并真真切切地使批评家们将其理论付诸实践。(14)
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一位略晚于李格尔的同代人,成为风格学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与强调艺术品的材质和技术不同,沃尔夫林着重于艺术品的线、轮廓、面、体积、重量、动感、造型、明暗、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等基本艺术语言的研究。沃尔夫林《艺术史的原则》(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一书,初版于1915年,至今仍是风格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15)针对李格尔“艺术意志”的理论,沃尔夫林指出,“人总是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他认为世上并不存在“客观的视像”,如同每个人都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一样,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皆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特定地区、特定时期艺术品的风格或形式,取决于特定的再现模式或视觉图式。对沃尔夫林来说,艺术史是看法或视觉化的历史,它关乎智力和精神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形式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而且也是富含意义的:
尽管具体可感的物质世界是眼睛赋予的具有特定形式的晶状结构,但每一种新的晶状形式都清晰地呈现出物质世界不同层次的视觉内容……视觉自身有其历史,而揭示这些视觉层次才是艺术史的首要任务。(16)
通过对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视觉再现形式的系统分析和归纳,沃尔夫林提出了著名的五对风格范畴理论。第一对范畴是线性(linear)与绘画性(painterly)。从线性到绘画性,或者如李格尔所说从触觉的知觉形式到视觉的知觉形式,它的发展程序乃是沃尔夫林所谓“为了纯视觉上的外貌,而放弃实体的可触知性”。(17)通过对欧洲15—17世纪艺术品基本形式的分析,沃尔夫林将其划分为早期文艺复兴、盛期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三个时期,并分别冠之以古风、古典和巴洛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拒绝使用“萌发”“繁荣”“衰退”这种生物意义上的概念,因为它们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他还提出,作为一种基本的风格发展模式,古风—古典—巴洛克的图式不仅适用于西方其他地区诸如古代和哥特式艺术,而且也适用于非西方艺术;并且,这种发展一旦完成便又会周期性地重新开始,“好像又能够从起点重新开始”。(18)
沃尔夫林曾经因为无视天才艺术家的作用而饱受批评。[赫尔曼·沃萨(Hermann Vosa )1920年撰写的题为《有名的艺术史还是无名的艺术史》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19)]但是,这种指责是与沃尔夫林主要的议题不相关的。沃尔夫林无意去关注个人的贡献或技法,他把这些问题留给了鉴赏家、收藏者、博物馆员及古董商来解决。
比他的风格理论更重要的是沃尔夫林留给艺术史一套全新的观看艺术品的方法。他关于“看法”的历史观是一个成功的思考模式,借助于这一模式,我们可以直接领悟艺术家的视觉结构机制。这一理论是否完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那些充满智慧的洞见,已被公认为现代艺术史学科不可或缺的共同财富。
三
通过渐进地吸纳及长时间激烈地论辩,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者们已经接受了艺术史的这种分析方法。涉足中国艺术史领域的早期学者,很多人来自文献学、历史学或文学等其他学科。他们开始尝试风格分析时,常常无视艺术史的这些原理,而这些原理恰恰又是他们借用而来的分析技巧的基础。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后的30年中,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学中赢得了地位,成为一门受人尊重的学科。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伴随着对盛行一时的极端科学怀疑论思潮的反拨,中国早期艺术史开始了它的长时间的重构历程,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便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先驱者。20世纪30年代,高氏根据铭文材料逐字逐义地重新检讨商周青铜器。作为一位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高本汉通过搜集、汇编铭文材料展开对商周青铜器里程碑式的工作。高本汉的研究主要依赖于郭沫若1932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他首先对商周青铜器铭文进行单独的分类,以期为青铜器进一步分类建立一个文字上的编年序列。(20)
可是,与周代青铜器铭文可提供丰富文献资料和明确纪年不同,商代有铭青铜的数量非常有限,铭文内容简短且极少有纪铭铜器。为此,在《中国青铜器新论》(1937)一文中,他集中研究“古典时期”(晚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高本汉抛开铭文分类的方法,着眼于从有铭铜器的纹饰型式来判断无铭铜器的年代。他写道:“这样的想法促使我首先必须对各种纹样做一个统计学上的分析。”(21)
根据对1285例样品的统计分析,高本汉将这些纹饰分为A、B、C三组风格类型:A组为原生型风格,B组为衍生型风格,两者是相互排斥的,C组为中间型风格,可与A组或B组并存。他创设了自成系统的理论假说:A组中的“写实性”饕餮纹(可以辨认的所谓“兽面”纹)要早于B组中抽象化的“分解”饕餮纹。在其后的两篇文章中(1959年、1960年),高本汉又通过对纹样装饰部位与器物形制相互关系的考察,以进一步确证早年的假说。(22)
对于研习中国早期艺术史的学者来说,1935—1937年无疑是一段令人激动而难忘的美好时光。1935年11月,伯灵顿中国艺术展览馆(The Burlington House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将馆藏的许多重要的青铜器拿到英国伦敦展览。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首次在西方世界公开亮相。不久,河南安阳殷墟的最新考古发现也通过一些学者的文章陆续介绍到西方世界,如田伯烈(H.J.Timperley)《苏醒的中国考古学》一文刊于《伦敦新闻画报》周刊(1936年4月4日),顾立雅(H.G.Creel)一本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可信通俗著作《中国的诞生》也于1936年出版。除了高本汉的研究外,其他令人振奋、颇具创见以及富含争议的学术成果也陆续见载于世界各地的学术杂志上。(23)
与高本汉“写实先于抽象”的观点完全相反,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抽象性的装饰纹样早于而不是晚于充分发展的写实性“动物”纹样。风格史研究者巴霍菲尔(Ludwig Bachhofer)、罗樾(Max Loehr)、戴维森(J.Leroy Davidson)等人指出,高本汉对纹样母题的统计是无意义的,其结论也是不恰当的。正如戴维森1937年所指出的,高本汉致力研究的那些装饰母题,其元素构成“很容易被后来的模仿者复制”。(24)1940年,针对高氏《中国青铜器新论》一文,戴维森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批评意见,指出B组的“分解”饕餮纹(高氏的B1式)实际上要先于A组的纹样,而“长尾”鸟纹(高氏的B3式)明显从A组纹样中演变而来。戴维森由此得出结论:“高本汉的B组纹样,实际上由两种不同类型的纹样组成:一类风格(B1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早商的纹样,要早于A组、C组风格;另一类风格(B3),则从周代初期发展而来。正是这种次生的B组风格构成了抽象性纹样的基础,并且相互交杂于中周时期。”(25)
对中国青铜器的风格发展做出连贯一致的解释,是沃尔夫林的高足巴霍菲尔。在《中国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1935),巴氏套用了欧洲艺术史的风格发展模式,指出中国青铜器是从低级的古风风格逐渐发展到高级的古典风格,并最终发展为繁缛的巴洛克风格,“生硬的角状纹样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充盈于整个器表的流畅纹样”。(26)这种进化方式不仅体现在青铜器纹样上,而且在象牙器、骨器和陶器上也得到印证。1944年,巴霍菲尔对其风格理论又进行了拓展和完善,提出古风式—古典式—巴洛克式三个阶段,可以分别对应于线性(平面)—塑形(三维)—装饰风格;其后的第四阶段,一种“简朴”或新古典式的风格样式开始出现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上。(27)1946年,巴氏宣称青铜器纹样的风格变迁“呈现出逻辑有序的有机进化过程”。(28)他将中国青铜艺术划分为呈周期性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商代,从古风到古典,再发展到巴洛克式;接下来为西周,从一种新的“简朴”的结构形式开始,到以复杂的非结构形式结束;第三阶段,大致相当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2年到公元前481年),从新郑风格开始,到李峪晚期风格结束,此时的动物纹样变得难以辨识;金村风格的出现标志着第四阶段的开始,其时间大致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81年至公元前221年)到公元8年西汉结束。(29)
不幸的是,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可能出于对德国抽象思辨传统的不信任感,巴霍菲尔过于大胆的风格理论,也因此成为古老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实证主义思潮复兴的导火线。巴霍菲尔的风格分析理论带有历史决定论的色彩,在他看来,风格演变是按照预设的进化“定律”,以一种似乎不可抗拒的自发力量向前发展。1947年,本杰明·罗兰(Benjamin Rowland)评论巴霍菲尔《中国艺术简史》时写道,巴氏的“方法归根到底是类型学的一种……一种从历史真实中抽离出来的风格进化史”。本杰明·罗兰指出,“任何艺术作品总是首先要去适合一种先验的框架,简直就是所谓萌发期—繁荣期—衰退期等风格发展概念的翻版,而其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即被建筑史家乔弗莱·司谷特(Geoffrey Scott)作为‘生物谬误’而摈弃。”(30)罗兰认为巴氏的理论根本无法应用到中国艺术上来,因为它忽视了其独特的品质和起源。
此外,巴氏对铭文的忽视也激化了文献学家和艺术史家之间的矛盾。梅兴—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1945年发表《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几点评论》一文,指出了青铜器风格与其铭文之间的巨大差异。梅兴—黑尔芬不同意巴氏“纯粹的类型学方法”,指出“(巴氏)阶段性的进化模式,使得那些风格相同但纪年时间不同的青铜器,或者那些纪年相同但风格不同的青铜器无法在其中找到相应的位置”。(31)1947年,约翰·波普(John A.Pope)发表《汉学还是艺术史学:中国艺术史学研究方法论刍议》一文,以同样的口气批评巴氏的学说,认为他所讨论的青铜器,远远超出了其分类的范围。(3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巴氏关注的是青铜器型式而不是铭文,但他对其接触到的纪年铜器的分析却是最成功的。(33)而他对创作年代更具体的中国雕塑(较之于青铜器)简明精到的分析,至今仍是该领域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尽管沃尔夫林自己并没有想到用他的风格范畴理论来判定作品的年代,但巴霍菲尔却能创造性地用它来分析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而且,对于20世纪40年代刚刚起步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而言,巴霍菲尔对中国艺术的把握是否准确、完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沃氏关于“看法”的分析方法,并对风格理论获得了明晰深刻的领悟。
巴霍菲尔最杰出的学生罗樾,意识到沃尔夫林的一般风格概念并不适宜解释特殊的风格发展。(34)为了避免巴氏机械套用沃氏理论研究中国艺术所存在的不足,1953年,罗樾以李济的研究成果《小屯出土之青铜器》(1948年)提供的第一手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将安阳殷墟青铜器划分为五个连续的风格发展序列,即从细线纹饰发展为轮廓鲜明的塑形性装饰。(图1:罗樾的五期论)他援引戴维森将线性浮雕装饰(罗樾称之为Ⅰ型)看成是“中国青铜器最早的风格类型” 这一“极富洞察力的假说”,并且指出,Ⅲ型和Ⅳ型包含在巴氏“图绘性风格”范畴之中。(35)罗樾在文末所论证的风格发展序列完全不同于高本汉的分类结果,高本汉所谓的“早期”A组纹样,仅仅是罗氏序列中最后的两种类型(Ⅳ型、Ⅴ型),而高氏所谓的“晚期”B组纹样,则散布于罗氏的五个阶段中。
通过对安阳殷墟青铜器五个发展阶段的划分,罗樾察觉到“一个完整而又连贯的风格进化序列”。巴霍菲尔“由线性到绘画性”风格进化的概括观念,在这里被转换成对商代青铜器装饰五个阶段之技术及风格发展程序令人信服的说明:Ⅰ型简单抽象的线性特征发展到Ⅱ型、Ⅲ型阶段,成为均匀浓密的复杂纹样而填布于器表。Ⅳ型阶段,一部分纹样退居为地纹,主体纹样较为醒目。Ⅴ型阶段,花纹已从地纹上凸出,轮廓更加鲜明,出现了高本汉所说的纹样发轫阶段的风格面貌。
正如预料的那样,罗樾全新的风格发展序列遭到传统论者的强烈反对。高本汉批评道:“一位自信的艺术史家居然将安阳青铜器划分为六个不间断的风格序列。”针对罗樾的说法,“一种风格不能依靠统计的方法获得理解,大量数字事实上并不比充分分析、理解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更多的风格内容……”,高本汉不客气地斥之为“无知”。(36)
但是,20世纪50年代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很快证明了罗樾早期风格序列的有效性。在河南郑州一处商代遗址中——该遗址不久被历史学家认为是殷墟之前的早商都城亳,(37)出土了属于罗樾所说的早期风格的青铜器。1974年,湖北盘龙城出土大批青铜器,其风格特征和郑州出土物完全一致,这些青铜器大多属于罗樾风格序列中的Ⅱ型。(图2—1、2、3:湖北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同年,郑州地区又出土两件属于罗樾Ⅰ型风格的青铜方鼎。(图3-1、2:郑州出土方鼎)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1件青铜爵,这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青铜器,纹样呈现出罗樾Ⅰ型风格那种窄条状的细线浮雕特征。(图4:二里头出土铜爵)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逐渐被说服接受罗樾的观点。例如,亚历山大·苏培(Alexander C.Soper)1966年这样写道:(罗樾)从已知的异常庞杂的青铜器中筛选出来的器物型制和大多数装饰母题,已准确无误地被中国方面的新证据所印证。考古资料累积的分量使我们更加确定,Ⅰ型与Ⅱ型阶段不仅仅是重要和可信的,而且,也使我们知道了迄今为止关于中国青铜艺术发轫时期最确切的情况。(38)
四
如果说米海里司第一个“世纪考古发现”导源于追寻和探索辉煌的古希腊文明,那么,考古学的第二个世纪同样得益于郭沫若揭示“中国地下宝藏”的召唤。但是,调查、清理中国大量的地面、地下文物着实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文献史学家要博览2500多年来的经书、史籍;艺术史者则要理解艺术作品本身各自不同的形式语言,他们不仅要对艺术作品进行分类、比较,将风格发展理论化,而且还要从其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阐释风格的变迁。这方面的工作还极少起步。虽然不计其数的材料充盈在我们周围,但从古代到更近的王朝时期,在很多领域还缺少充分可靠的实物证据,即便有,我们还没有加以充分地理解。
在1954年出版的《金文丛考》序言中,郭沫若谦虚地将《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划时代巨著称为一本“工具”书,哀惜对早期青铜器缺乏一个系统的论述。(39)同样地,在中国古代木雕、文学史插图、戏剧以及小说等领域卓有建树的郑振铎先生,也谦虚地将其学术著作说成是“资料”或“研究材料”。在其担任国家文物局首任局长期间,郑先生虽然很少再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但他大力提倡整理和翻印古籍图书。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不无抱怨地写道:
(学术研究)看来人人会做,但做得好或做得不怎么荒唐的却是太少了……对不起古人,也就对不起今人。对古人不负责任,也就是对今人不负责任。(40)
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场针对巴霍菲尔《中国艺术简史》方法论的大论辩之后,美国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开始意识并追随本杰明·罗兰的忠告:“完全照搬沃尔夫林的风格模式分析中国艺术史,肯定是行不通的”。(41)代之而起的,是对更可靠的基础资料的收集以及特定主题的研究。摆脱理论玄思,有助于消除把中国艺术史看成是西方艺术史等同物的观念,促使中国艺术史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由风格史家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风格分析技巧,对于现代学生而言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合理界定风格基本概念的前提下,熟练运用风格技巧能够获得富有洞见的批评意见。反之,忽视或错误理解其理论原则,单凭技巧的完善则不能希冀获得对主题的彻底领悟。
昨天的假说成了今天的方法。罗樾对商代青铜器风格发展阶段的划分已被考古证据所证实,成为描述商代青铜器风格发展一种广为接纳的方法。虽然周代青铜器的风格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一个连贯的解释在巴氏《中国艺术简史》中已初显端倪。在那本书中,巴氏假定了一个在逻辑上易于理解的风格演变序列。他对先周政权及其它地区青铜文化的区域性传统的考察与新知,使我们对西周青铜艺术的多样性问题及周代对殷商青铜器风格的继续和发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其关于东周时期新郑—李峪—淮—金村的青铜发展序列,已经在河南西部上村岭、山西侯马、河北景山、河北平山、湖北随县、安徽寿县及其他南方地区获得更多的重要实物材料。
秦始皇兵马俑的惊人发现向世人昭示,早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之前就已出现了充分发展的纪念性雕塑。(图5—1、2、3、4、5、6:秦始皇兵马俑)而在此之前,巴霍菲尔对汉代大将霍去病(病逝于公元前117年)陵墓的大型石雕(这其后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存世最早的纪念性雕塑)的描述并非夸大其辞:他指出陵墓的大型石雕具有“令人震惊的原始主义”,(42)他所察觉到的这一特征,与约为公元前3世纪末1件在蟾蜍身背跳舞的小型青铜男孩塑像(巴氏赞誉其有“闲适灵动”的表情)形成强烈的反差。(43)但随着秦始皇兵马俑恢弘雄伟的雕塑群的出土,巴氏对小型青铜雕塑和“粗劣的”大型石雕在技巧方面所感知(perceived)出来的差异被证明是不可靠的。
尽管秦代人物雕塑是一个令世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但其制作方法表明中国的人物再现技巧,并没有突破我们原先的框架概念。巴霍菲尔认为中国上古雕塑遵循严格的对称性或“正面律”,这点同样适用于秦代的人物雕塑。1900年,伊曼纽·鲁惟一(Emmanuel Loewy)对存在于几个不同文化中的关于上古人物再现的“正面律”现象进行了心理学上的阐释。鲁惟一指出,古代艺术家乃根据“记忆形象”从事创作,其所制作的形象可以很容易地与其他形象区分开来。(44)所有的这些再现作品皆遵循一些共同的特征:从观众来看,人体各部分形态或正或侧,都是平正面、清晰而典型的图案式母题,各部分都显示出其“概念化”的特征;人体被分为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重要的主题,在局部的基础上组合在一起,既显示不出有机的整体,颈脖、手腕或者踝关节也缺乏有机的联系;没有透视,斜向缩小被扭曲了,连侧面也保留着原样;人物空间动作不用三维形态来表现,而是通过二维、无机的平面轮廓线的节奏来体现。(45)
从东周末年(公元前6世纪)到六朝后期(公元550年)大约千年的时间内,中国人物画表现一直停留在线条的、二维空间的、夸大前景形象的古风阶段。在这以后,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圆柱型风格出现,人物各部分之间也相应出现了有机的联系;最后,演变为初、中唐时期(在7世纪末8世纪初)的三维立体造像形式,此时人物的各部分形态变成了有机的、多方向的互相关联的肌躯结构。这种风格发展阶段可以在连续有序的纪年佛教造像上得到准确无误的验证,与此相伴的,这时期的人物画也显示出相同的风格特征。
正如前文所言,罗樾避免了巴霍菲尔机械套用沃尔夫林关于风格以周期性结构和不可抗拒的自发力量发展的理论模式。阿诺德·哈兹尔(Arnold Hauser)将风格解释为“一种不断变换内容的动态关联的概念”,罗樾以此来分析中国艺术史中连续不断的“风格变化特性”。根据罗樾的观点,新石器时代到周代,风格是“原始再现性中的形式本质”;汉代到南宋,风格就像是“一件工具,好比发现或把握现实的一件工具”。(46)不同于其对商代青铜器风格发展序列的精到分析,罗樾关于中国艺术史“风格变化特性”的理论,却无助于描述风格的变迁。罗氏的理论非常复杂,在此难以展开充分讨论,但他认为装饰和再现艺术存在差别的立场,我们还是有必要加以关注的。(47)罗樾认为,“中国古代(即汉代以前)没有再现性艺术(或塑形摹写),只有赋予了艺术家情感的、可以称得上艺术的纯粹性装饰”。他写道:“在整个古代以前,中国尚无图绘性艺术的迹象,只(在图解的水平上)有某些非再现性非艺术。”(48)对装饰艺术最终屈从于图绘形式的阐明,是罗樾对中国艺术史研究有益的贡献,但其“再现性非艺术”却完全陷入到美学而不是艺术史范畴。在风格史中,装饰(几何的或程式化的)艺术不可能从再现艺术中分离出来。(49)
在罗樾看来,商代青铜器装饰不存在对外在现实直接的暗示,它们只是“纯粹的装饰……或者仅仅是图案本身”。罗樾援引兰格尔(Suzanne Langer)的一段话,“对装饰艺术和原始艺术的比较研究,有力地说明图形是第一位的,再现功能由此而产生。”罗樾相信,最早的动物形象“仅仅是由雷纹和一双或多双眼睛构成……它们绝不抽象,只是纯粹的设计……这些装饰没有任何象征或图像的含义,或者仅有作为纯粹形式的意义”。(50)关于青铜器纹样的起源及其含义,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马承源认为,商代青铜器动物纹样具有驱邪的象征意义,在《辉煌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一文中,他以春秋晚期的实物材料对之进行了论述。罗樾的学生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则赞同其师的观点,认为商代青铜器纹饰是一种纯粹的图案艺术。
由于商代青铜器是一种工业化的艺术形式,自然地,我们理应考虑森佩尔的观点,“技术,在一定范围内决定着艺术发展的规律”。(51) 威玛·凡尔班克(Wilma Fairbank)曾指出,一种通过研究中国青铜器设计的方法可以检验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诸如考察作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如此,器物凸棱被用来处理范之接合处青铜溶液的渗漏;铜器装饰中同位并置的基本原则显示外范的块状分割;最后,主体饕餮纹样的双目可能“被用来充当或标示装饰范块在模面位置的中心参照”。威玛·凡尔班克推断,“倘若如此,工匠们对青铜器正、侧面动物母题双目的设计,可以认为是通过示意联想演绎发展起来的”。(52)
但是,正如李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的创作过程也许与技术论者的假定正好相反:取代形式总是伴随技术而生,技术可以通过发明以服务于艺术家心目中的形式。(53)罗樾认为晚商青铜器动物纹是由早商青铜器一种“(对现实)初步的、模糊暗示的半几何形纹”派生而来,在他看来,这种半几何形纹的母型导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的小雷纹、菱形纹、锯齿纹、Z曲折纹、波浪纹和其他几何形纹。(54)实际上,罗樾可能会赞成威玛·凡尔班克关于动物形象“通过示意联想演绎而成”的观点,尽管推论原因不同。商代艺术家将纯粹设计中的一个动物形象看成是一种“罗沙”测试(一种从对图画的反应来分析性格的心理学测验),并最终发展为罗樾称之为Ⅴ型的充分发育的饕餮纹风格。(图6,1-2:安阳时期铜罍、铜鼎)
5世纪,硕儒颜延之(384—456)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一种广为接受的阐释。他认为有三种图像符号(“图载”):第一种是表现自然的法则(“图理”),即《易经》中的八卦;第二种是表现自然的概念(“图识”),即书写的文字或标记;第三种是表现自然的形式(“图形”),即所谓的绘画。(55)根据颜延之的解释,没有任何形象或图形(图)是“纯粹的设计……作为纯粹形式的意义”。正如马承源所指出的,青铜器常见的装饰母题“圆涡纹”(图7-1:青铜器上的“圆涡纹”,湖北盘龙城出土,图7-2:局部)实际上可能是象征火焰的图形化。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考工记》,有“火以圜”(56)的记载。果若如此,那么对于目前还知之不多的既表“图理”又示“图形”的青铜器装饰纹样,有可能将中国文字或标记(“图识”)的起源清楚地揭示出来,反之亦然。(57)
我们也可以大胆地将罗樾关于商代青铜器令人信服的五种型式风格置放到中国文化的上下文中进行探讨。商代青铜器铸造是一个两分步骤:制模作范,即陶器阶段;(58)铸器,即冶金术阶段。青铜器装饰的所有技术因素都可以从陶器阶段的模、范制作中得到理解。通过对模(正像)和范(负像)的雕刻来获得成品青铜器所期许的装饰纹样(正像),可谓是中国最早的几门工艺之一,它牵涉将纹样从一个面转化到另一个面的问题。譬如,雕刻的印章(负像,浮雕或凹雕类型)压印在泥片上(正像,反转的浮雕或凹雕类型)或者纸上(正像,正转的浮雕或凹雕类型);再如,雕刻于石质或木质上的书法(正像,大部分为凹雕,较少为浮雕)制成拓片(正像,正转的凹雕或浮雕类型);又如,木版印刷(负像,浮雕)转化为印刷书籍(正像)。从商周青铜器,经过汉、六朝到唐代的纪念性碑刻,以及随后书法汇编的集大成,到1679年《芥子园画谱》及其后的各种版本,雕刻艺术成为中国文化一种重要而连贯的传统。两千多年的书法发展史,学者们很容易地掌握了从毛笔到刻刀、从刻刀到毛笔的书法运用技巧,并由此确立了笔法和刀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雕刻者而言,首先必须对轮廓外形拥有高度的敏感力,并且熟稔和喜爱阴、阳图案之间的相互转化。
罗樾于1953年之文,论及了一件“非典型”的商代青铜器实物:“可能引发的争议是,这件爵同时具有Ⅰ型和Ⅱ型的风格特征;它们是相互交叠的,不同的只是技巧方面的差异。”(59)如果Ⅰ型的细线浮雕施刻在外范上,Ⅱ型的宽带阴线纹样施刻在母模上,那么,Ⅰ型、Ⅱ型在范块上的雕刻纹样,将分别对应于阴(阴雕或凹雕)和阳(阳雕或浮雕)。如此,Ⅰ型、Ⅱ型作为共生、互补的技术,则隐含着一种二元的思考方式:不仅Ⅲ型是对Ⅰ型、Ⅱ型风格的自然合成和发展,而且Ⅳ型、Ⅴ型在它们的初始阶段,仍然是一套相互共生、互补的技术。
贝格利通过技术上的观察,似乎确信Ⅱ型图案仍然雕刻在外范上,但是,就我们眼睛所见,展览中所有三件Ⅱ型青铜器(见图2),其图案皆刻在母模而不是外范上。铜钺的刃部布满了花纹,要想在外范上雕刻凸起的花纹简直不可思议。(图8:铜钺拓片)其他迹象表明,它是在母模上运用了凹雕技术:刻刀进、出的痕迹和方式;手轻微地滑动或用方形刻刀将泥片划成小块,导致雕刻线条偶尔的摆动或粗糙的边缘。将带有扁平底部的条状图案从外范的弓形器表挖出,即便有此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例如,铜斝上“旋涡纹”那种平滑圆形的外表,也许是在青铜器铸成之后对器表进行了整修。(见图2,2)
如果不考虑实际运用的技术因素,那么,在铸造和装饰青铜器的过程中——从模(又称母模)到范,陶土到青铜、形象到映像、工艺到典礼、物质到精神,其间阴阳的交互、置换与互补毫无疑问是相当重要的。以此而论,二元主义、对称性、可逆性、增补性等原理的出现,是翻范、合范技术的原因而不是结果。罗樾的Ⅲ型纹样——以扩展到器面的饕餮纹为标志,其显示出在凸雕与平雕、浮雕与凹雕之间逐渐增强的二元作用——可能同时制作于制模和作范阶段。湖北出土的一件铜卣(图9:铜卣,湖北盘龙城出土),贝格利将其归为Ⅲ型风格早期,腹部饰有一圈异常精致的Ⅱ型饕餮纹饰带,两边镶以窄条状的凸起的小联珠纹,颈部饰有三道平行的Ⅰ型凸弦纹,肩部有较窄的夔纹饰带,带饰上缘镶窄条状的凸起小联珠纹。对主体饕餮纹的设计,艺术家在浮雕表面增加一些自由的线条,从而将浮雕和凹雕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将浮雕花纹之间的雕刻裂隙转变为狭窄的流畅线条,有时候作单独的装饰;整体效果是流畅且富有生机的繁缛花纹,将突出的两目团团包围。出土于湖北藁城的一件铜瓿(图10,1-2:铜盘,湖北藁城),饕餮纹的主要部位——鼻、面、嘴、角、耳等——皆用浮雕的方式突出,饰地衬以Ⅲ型的雷纹和羽状纹,饕餮纹既采用浮雕、凹雕,也留有空白。盘的肩部有浓密图表式的Ⅱ型饰带,带饰两边镶以Ⅰ型窄条状凸起的联珠纹带。再者,铜罍上突出的羊首面部是雕刻的阴线图案花纹,而腹部则饰以Ⅱ型的凸起雷纹和羽状纹。(图11,1-3:铜罍)
山西出土的一件铜壶(图12,1-2,铜壶,山西出土),算得上是阴阳互动的好例,实与虚、凸与凹、浮雕和阴刻,显示出有力而又和谐、繁杂而又有序的相互渗透。罗樾于1953年之文,列举了一件与之类似的藏于旧金山狄扬美术馆(M.H.de Young Memorial Museum)的“非典型”铜壶,其显示了从Ⅱ型到Ⅴ型的复合风格面貌。(60)对两件壶所具有的复合风格特征,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由于两者皆出土于山西境内,因此它们代表着一种“古怪的”地区风格。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们也为研究Ⅳ型、Ⅴ型风格的开端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通过对湖北藁城铜盘(见图10,1-2)型式发展的考察,他们对以雷纹为地的“饕餮”面主要特征提出进一步的阐释。饕餮的耳、目凸显于器表之上;脸部、蝉及雷纹地充盈于器表;排齿和开嘴在器表中处于次要的地位。整个图案设计显示出对阴、阳图像相互间细微变化的熟练掌握:凸起的“U”形耳被相同形状的凹陷排齿所衬托;器物上半部平整光滑的面部与其下隙空填刻的雷纹形成鲜明的对比;平滑一致的脸部被浅浅的凹雕和浮雕图案覆盖,而填刻雷纹的隙空则被精致醒目的蝉、耳形状所点缀,前者系浅雕,后者则留空。假如面、蝉及雷纹地表示Ⅳ型风格,双耳预示Ⅴ型风格,那么,它们只是同一发展状态中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
五
正如罗樾所言,艺术史家面临的实物材料毫无疑问具有“一致性、连贯性、逻辑性”之风格特征。自罗樾1953年文章发表以来,尽管实物标本及其地区性种类的知识有了巨大的增加,但它们只是部分调整而没有否定罗樾关于商代青铜器风格演变的理论体系。这种令人信服的风格序列——它们不是依靠文献记录而获得自证——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当一种风格目标或动机清晰可辨,并且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其演变才不太会因为延续与复兴这些经常存在的问题而变得过于复杂化。统观中国艺术史,实际先后出现了三次大的风格转变:首先,乃罗樾所说的商代青铜器发展序列论说;紧承其后的,为巴霍菲尔关于5—9世纪人物画形似再现的发展;最后,自唐以前(6世纪)山水画的象形母题至元代(14世纪)山水画对幻觉空间的征服。(61)
描述中国艺术史,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服务于其他诸如文学、思想等文化活动的结构。简单地纵览一下中国人物画、山水画、书法、诗歌、散文和思想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共享着同一种发展模式:在经历一个初步的发展阶段之后,它们都经历了连续的“复古”或“回到古代”的运动。我认为中国艺术史中存在两种类型或两种动力的复古:一是力图批判性地学习过去来创造伟大;一是通过心理上的退隐和自我的内省图解古老的传统。(62)我所提出的关于风格史的一种结构,不仅可以有效地描述风格的变迁,而且可以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背景中阐释风格的成因。
中国艺术史一个永恒的真理就是,当母题保持不变或被重新复兴,风格变迁依旧。1953年,罗樾写道:“确实,我们将不得不认真对待不断扩展的母题宝库:不朽的古老母题同新生的母题相与共存,当这些后来者被发明以后,古老的母题不必退隐遁迹。”(63)由于风格发展地区性因素的存在,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山西出土的一件铜壶(图13,铜壶,山西出土),上面的Ⅱ型风格的带状纹样就可视为地方化或有意识复兴的证据。只有在考古学家和风格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方可为风格特性分析提供坚实可靠的知识背景。
注 释:
(1)朱剑心:《金石学》,香港出版,1964年版,第21页;又见Robert Poor ,“Notes on the Sung Dynasty Archaeological Catalogs”,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9,1965,pp.33-44.
(2)朱剑心:《金石学》,香港出版,1964年,第21页。
(3)夏鼐:《沈括和考古学》,《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第1—17页。
(4)夏鼐:《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考古》1959年第12期;吴岩:《忆西谛先生》,《文物》1961年第11期,第1—3页。
(5)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悼念郭沫若同志(1892—1978)》,《考古》1978年第4期,第217—222页。
(6)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郭沫若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7)同(5),第218页。
(8)郭沫若:《交流经验,提高考古工作的水平——在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第5—9页。
(9)郑振铎:《考古事业的成就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考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第9—16页。
(10)Aldolf Michaelis,A Century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trans, Bettina Kahnweiler,London,1908,pp.304,340.
(11)Gottfried Semper.Der Stil in den technischen kunsten,Munich ,1978,Vol.I.pp.vill ff.
(12)与森佩尔将材料、技术和功能看成是艺术创造的先决条件不同,李格尔将材料、技术视为艺术创造中的限制性因素,“艺术意志”在与材料、技术的斗争中奋力为自己开辟道路。李格尔在《风格问题》中批判了森佩尔及其追随者,指出即便是“线绣的图案也要依赖于制作它的人的艺术观念”,“无论是画笔或尖笔,它们自己都不会创造,必定要由人手控制,而手又要依靠艺术灵感,即那种要从传统和精神感悟中创造出一些新东西的不可遏制的冲动。”
(13)Paul Frankl,The Gothic:Literary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Eight Centuries, Princeton,1960,p.606.
(14)同上,p.626.
(15)Heinrich Wolfflin,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trans, M.D.Hottinger,repr,ed, New York,1950.
(16)同上,p.11.(17)同上,p.229.
(18)同上,p.234.
(19)Hermann Vosa,“Kunstlergeschichte oder Kunstgeschichte ohne Namen”,Kunstchronik and Kunatmarkt,31/1/22,1920,p.435.
(20)Bernhard Karlgern,“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8,1936.
(21)Bernhard Karlgern,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9,1937,pp.11 ff.
(22)Bernhard Karlgern,“Marginalia on some Bronze Albums”,Part 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31,1959,pp.259 ff,:foid..Part II,32,1960,pp.1-25.
(23)udwig Bachhofer,“On the Qrig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The Burlington Magazine, 393,December 1935,pp.251-263;Perceval Yetis,“The Bronzes”,The Burlington Magazine,68/384,January, 1936.pp.15-22;Max Loehr, “Beitrage zur Chronologie der alteren chinesischen Bronzen”,Ostariatische Zeitschrift,22,Journal-April 1936,pp.1-41;H.G.Creel, “Notes on Professor Karlgren’sSystem for Dating Chinese Bronz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B.C I.July 1936; Davidson, “Toward a Grouping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Parnassus 9/4,April 1937,pp.29-34,51.
(24)J.Leroy Davison,“Toward a Grouping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p.30.
(25)J.Leroy Davidson, “Notes on Karlgern’s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The Art Bulletin, 22/3,September 1940,pp.165-166.See alsoCutherine Crassl, “New Researchs on Chinese Bronzes”, ibid.251/1,March 1943.pp.65-78.
(26)Ludwig Bachhofer,“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p.257.
(27)Ludwig Bachhofer,“The Evolution of Shang and Early Chou Bronze”, The Art Bulletin, 26/2,June 1944,pp.107-116.
(28)Ludwig Bachhofer,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New York,1946, preface.
(29) 同上, preface, pp.53-54.
(30) Benjamin Rowland,Jr.,“Review of Ludwig Bachhofer’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The Art Bulletin, 29/2,June 1947,pp.139-141.
(31)Otto Maenchen-Helfen, “Some Remarks on Ancient Chinese Beonzes”, The Art Bulletin,27/4,Devember,1945,pp.239.
(32)John A.Pope, “Sinology or Art History:Notes on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1947,pp.383-417.
(33)John A.Pope, Sinology or Art History:“Notes on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0,1947,pp.383-417.
(34) Max Loehr,“Some Fundment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3/2[February 1964],p.186.
(35)Max Loehr,“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1300-1028B.C.)”,Archives of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7,1953,pp.42-53.
(36)Bernhard Karlgern,“Marginalia on some Bronze Albums”,Part 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31,1959,p290 n.2.
(37)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第10期,第24—42页;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53—73页。
(38)Alexander C.Soper,“Early, Middle,and Late Shang:A Note”,Artibus Asias,28(1966),p.7.
(39)郭沫若:《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40)吴岩:《忆西谛先生》,《文物》1961年第11期,第3页。
(41)Benjamin Rowland,Jr.,“The Problem of Hui-tsung”, Archives of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5,1951,p.5.
(42)Ludwig Bachhofer,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 p.61.
(43)同上,p.59.
(44)Emmanuel Loewy,The Rendering of Nuture in Early Greek Art,trans.John Fothergill,London,1907,p.12.
(45)On the basis of Loewy’s “memory picture”,George Rowley(1893-1962)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chanacterized archaic Chinese art as “ideational” visualization,(see discussion by Alexander C.Soper, “Life-motion and the Sense of Space in Early Chinese Representational Art”,The Art Bulletin, 30[1948],pp.167-186,For Rowley’s ideas about interpreting period styles in terms of the “growth of the mind”.see Rowley, “Art and History”,Record of The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1960,pp.76-83.
(46)Max Loehr,“Some Fundment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2[February 1964],p.186.
(47)同上,p.192.
(48)Max Loehr,“The Fate of the Ornament in Chinese Art”,Archives of Asian Art,21(1967/68),pp.8-19.
(49)尽管李格尔论述的古代东方地毯属于工艺装饰品性质,但他将“风格意志”和风格运动理论(从触觉到视觉的两极运动)同时运用到再现艺术史上。沃尔夫林的风格概念,同样可以从装饰和模仿的角度加以阐释。参见Heinrich Wolfflin,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trans, M.D.Hottinger,repr,ed.,New York,1950,p p.16,230.
(50)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New York,1968,pp.12-13.
(51) Semper, Der Stil,vol.I,p.vill.
(52) Wilma Fairbank, “Piece-mold Craftsmanship and Shang Bronze Design”,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18,1962,p.15. Fairbank summarizes many of the ideas found in Noel Barnard,“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merica China”, Monuments Serica Monograph,XIV,Tokyo,1961.
(53)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p.12.
(54)See Frankl,The Gothic,p.628.
(55)张彦远:《历代名画记》,W·阿克译,《若干唐代及唐以前文献》,伦敦,1954年,第65-68页。
(56)马承源:《辉煌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载《伟大的青铜时代》,方闻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57)Kiyohiko Munakata,“Concepts of Lei and Kan-Lei in the Early Chinese Art Theory”,Written for a Conference on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held on 6-12,June1979。(宗像清彦在文中指出,艺术家以“感”来体验多种物类基本的特性,不仅把握外部面貌,而且掌握了原型内在之“气”。)
(58)Fairbank,“Piece-mold Craftsmanship”,p.10.
(59)Max Loehr,“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1300-1028B.C.)”,Archives of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7,1953,p.50.
(60)同上,p.49.
(61)Wen Fong, “Toward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Art Journal, vol.28, no.4 ,Summer, 1969: 388-397;“How to Understand Chinese Painting”,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15, no.4 ,Aug., 1971: 282-292; Summer Mountains: The Timeless Landscape,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5.
(62)Wen Fong, “Archaism as a‘Primitive’Style”,in Artists and Traditions: Uses of the Past in Chinese Culture,ed.,Christian F.Murck,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oty,1976,pp.89-109.
(63)Max Loehr,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1300-1028B.C.),p.50.
方闻(Wen Fang),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荣休教授。
黄厚明,男,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谈晟广,男,浙江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